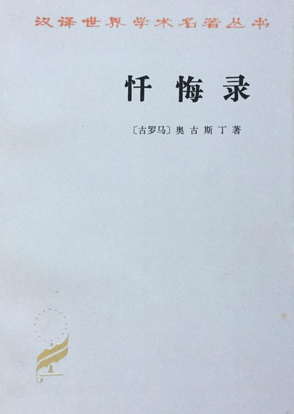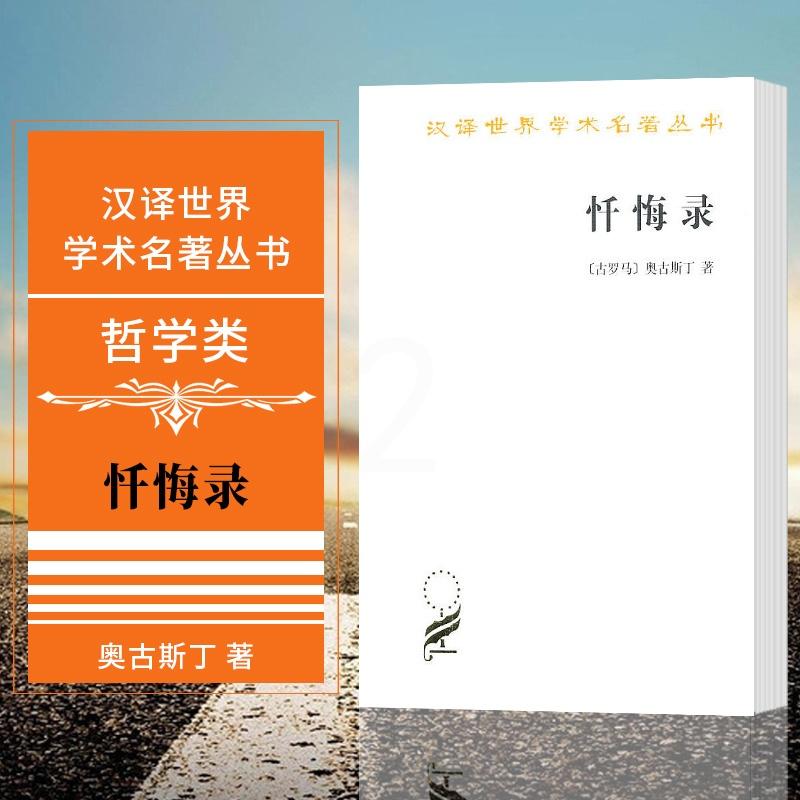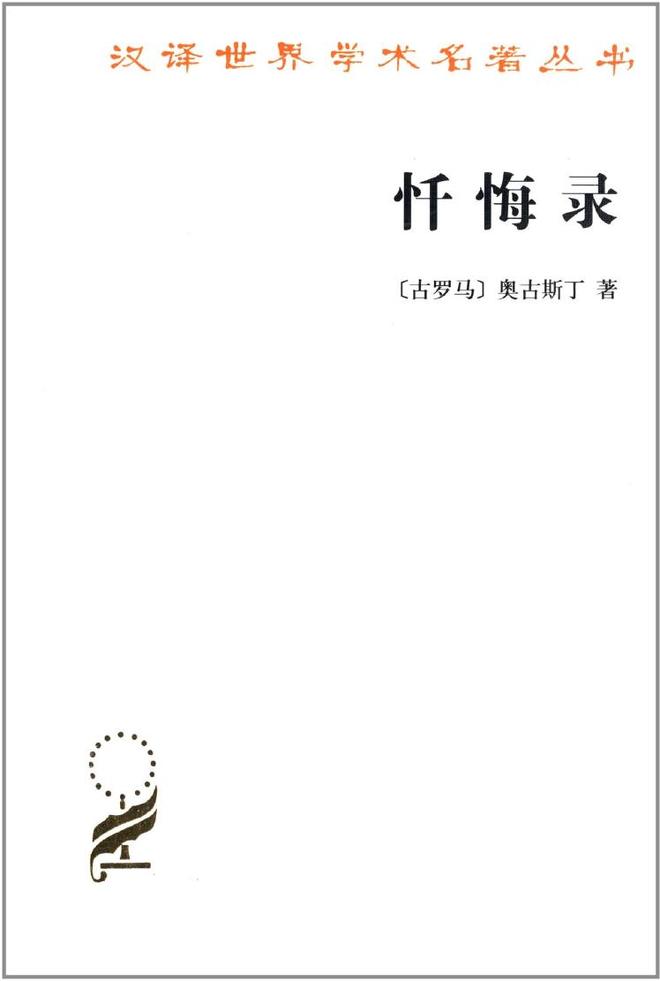作品主题
寻求幸福,得到上帝的恩惠
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一书中,奥古斯丁以“神”为假想读者,以第一人称“我”为忏悔主体,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聪颖过人,却痴迷异教、耽于情欲的年轻人,从怀疑主、发现主到信仰主、服侍主的精神历程。不过,这条漫漫途程却是起步于欲望的纷扰。对奥古斯丁而言,此种纷扰实乃源于他对暂时的有限的存在不满足所产生的内在焦虑和困惑。为试图改变这种境况,他转向探求不朽的永恒,进而寻求真理即上帝,并最终实现理解上帝和服侍上帝。在奥古斯丁看来,追寻上帝目的只有一个,即寻求幸福,得到上帝的恩惠。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只是为了人能正当、正义地生活。要相信,上帝给人自由意志不是为了人能借自由意志犯罪。没有自由意志,人便不能正当地生活,这是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的充分理由。人若利用自由意志犯罪就要遭神意安排的惩罚。上帝是世界万物的唯一的来源和塑造者,他是至善的,所以世界从根本上是善的。从本体论即创造本性上说,意志本身是自由的。从道德选择层面上说,自由意志本性的运用则是善,否则是恶。基督教认为善存在,恶是小存在,是善的缺失。其强调了上帝创世中,因其最爱人,赋予人以自由是出于善,自由本身是善的;且唯独人具有自由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本身也是善的,可以决定自己的行为。 既然自由意志是善的,自然滥用自由而犯罪的责任不在于上帝。奥古斯丁认为罪恶最初就是由于人不听上帝的话,滥用了自由意志。所以罪恶的即小是上帝造就的,也不是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人滥用自由意志的结果。即恶的来源是意志的败坏。在意志的选择上,上帝创造一切,包括意志,包括善。《忏悔录》中的“光照说”的例子则可充分说明上帝对善的选择。世间有恶,那是由于人滥用了自由的结果。上帝是至善,是唯一的本体,恶小具有本体性,恶不是本质,而是善的缺乏。听上帝的话就是善,否则就是缺乏善。如原罪,亚当和夏娃会犯罪,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意志。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意志的能力这里,奥古斯丁引出了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说明罪恶的原因。 赎罪观念
人既然有罪,就要赎罪。奥古斯丁通过《忏悔录》向世人言说他的罪行,同时也通过书中对上帝的忏悔祈求上帝的原谅,同时他也赞美了上帝,虔心皈依主,皈依上帝。承认上帝的伟大是忏悔的第一步,作者在书中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思想状况,不断地向我们证明,上帝是至大至善、全知全能、至仁至义、全隐全显、登美之峰、造强之极的。而且上帝也“不忍心自己亲手创造的一切趋于下流,而是以恩典之光照启受造物向善的心灵,让受造物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向善避恶,充盈自己的灵魂世界,让理性的意志控制激情冲动的肉体”而这又显示了上帝的仁慈。对每一个虔心悔过的罪人都张开双臂来拥抱他,正如《圣经》中浪子的比喻“只是你这个兄弟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人们想要祈求上帝的原谅,就要先认识上帝。当一个不信基督的人想要寻求这样一个伟大而崇高的主的帮助时,应当要先认识再信奉,有了虔诚的信仰之后才能去祈求他,但是只要认识主的人,最后都会走向信奉之路,及至走向最后对上帝的祈祷,到达精神的彼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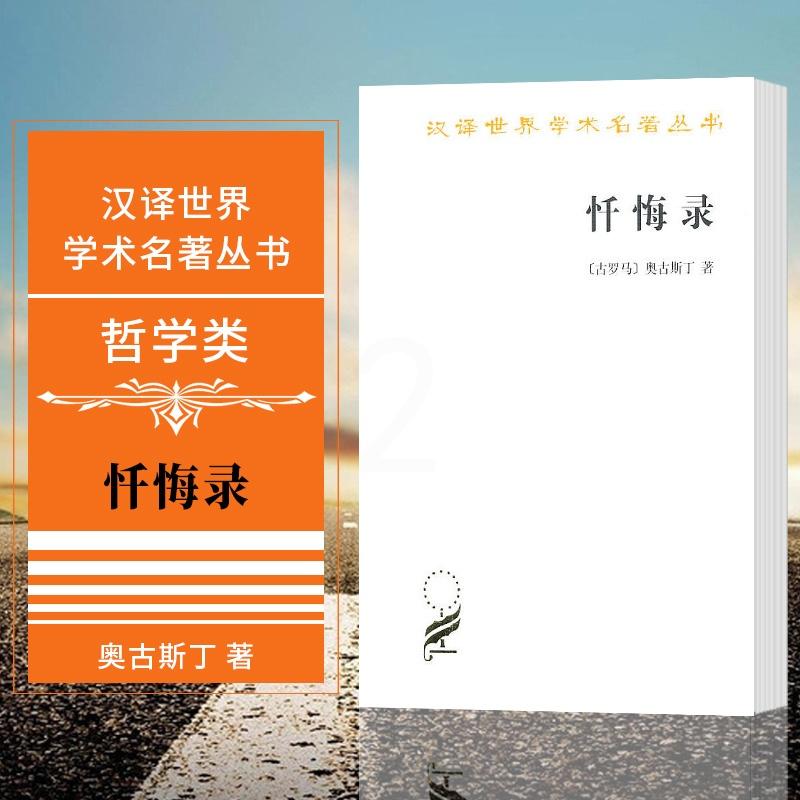
忏悔录
从全书来看,整本书就是对自己皈依天主之前所有恶行的赤裸裸的披露和忏悔,在坦诚的基础上搭建和天主沟通的桥梁,除了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探索和展示外,对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上帝创造一切,并非毫无秩序可言,其也是按照自然序列进行的。上帝按照一是天使,二是人,三是动物,四是植物,最后是矿物及非生命的无机物的先后顺序创世,并指出动物、植物、矿物及非生命的无机物都是为人服务的,人根据意志的爱好越来越接近天使,服务于上帝。因此,奥古斯丁认识到,在寻求上帝的道路上需要生存着的人的一种意志做出选择,这样最终才有可能与上帝发生根本的联系。
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清楚地表明,人作为宇宙中的一种存在,他的里面也存在这样一种秩序。人与万物不同之处在于,他具有灵魂。人的灵魂高于他的肉体,但低于上帝。因此,灵魂要主宰肉体,服从上帝。因此,上帝是至高至真的,他以不可违抗、永恒不变的法则主宰着宇宙万物,使肉体服从于灵魂,灵魂和其他一切事物都服从于他自己。
在奥古斯丁看来,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但不是一切意志的支配者。“一切的力量都来源于他,但不是一切的意志都出自于他。意志能选择不顺从,是因为意志中有一种违背自然的缺陷。人因为是从无中被造的,所以会被这种缺陷所败坏。当人的意志选择了不顺从,恶便产生了。从创造论的角度来说,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万物在本体上都是善的,恶在本体上是不存在的。然而我们说堕落是指一个事件;而原罪是因为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二者的堕落使最初的全善变得有缺陷。亚当和夏娃不听从上帝的命令,致使从始祖那里人类一出生就有了罪。即意志的背念是原罪的结果。
时间观念
奥古斯丁通过对简质的例证的分析而提示出人在时间中的历史,人有其时间,人的时间的每一时刻、每一瞬间都充满意义。而历史的最本质的意义在于,即使某些事物、某些已经成为者看似是必然而不依赖于人的,但是人依然有其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志及其由此而做出的自由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已经成为者并非是必然的,并非是诸多法则所限定的,以至于他们是如此这般而非如彼那般的,而是恰恰由于他是已经成为者而能够被测量,之所以能够这样说,是因为已经成为者的处所并非在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在人的记忆和回忆之中,对于他的测量则在人的自由的灵魂(精神)之中、在人的自由的人格之中。由此,所有成为者都在人的自由中是可能的,成为的过程就是变化的过程,变化是此间世界的现实,如果谈及必然性的话,那么最大的可能是,一种必然性存在于变化过程的持续之中。
所谓时间已经不在,或时间尚未存在,并非意味着取代“尚未存在”以及“已经不在”的必定是从灵魂反射而出、投射而出的作为灵魂的现象的某物,而是恰恰意味着被回忆者就是被回忆者,被观想者就是被观想者,被期待者就是被期待者;时间在灵魂中有其隐匿和遮蔽(灵魂隐匿在灵魂之中),但却并未成为灵魂、并非是灵魂。也就是说,在奥古斯丁的时间分析中,即使时间在灵魂中有其隐匿、有其遮蔽,但是时间却并非因此而是灵魂的流溢,灵魂的内在性并非吸附此在的存在者于自身之中,尽管世界被灵魂的行为(灵魂的活动)所关照、并被灵魂保持在此在之中,但是世界依然是被纳人感觉、思维和存在秩序之中的“外在者”(处于灵魂之外者),而且世界的客观存在方式自身也隶属于这一整体的绽放过程,人必须以秩序观念理解在整体的宇宙发展过程中的世界。
在此,灵魂对内在、外在世界对象的观照以及灵魂对他们的摄取,不乏神秘主义之色彩,人对世界的理解不乏客观目的论的色彩,奥古斯丁不愧同时为占典哲学的承继者和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不愧同时为中世纪神秘主义和理性哲学之开启者;姑且不论对奥古斯丁的这些评价而返回到我们的时间概念:无论如何,灵魂在建立起了与超验者、与上帝的联系,或者说,通过灵魂对于时间的测量暨认知,奥古斯丁在逻辑上收束了他对于时间问题的思考,并且将时间视为灵魂与上帝关系的直接表述,视为伦理宗教中人格行为和神人关系的核心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