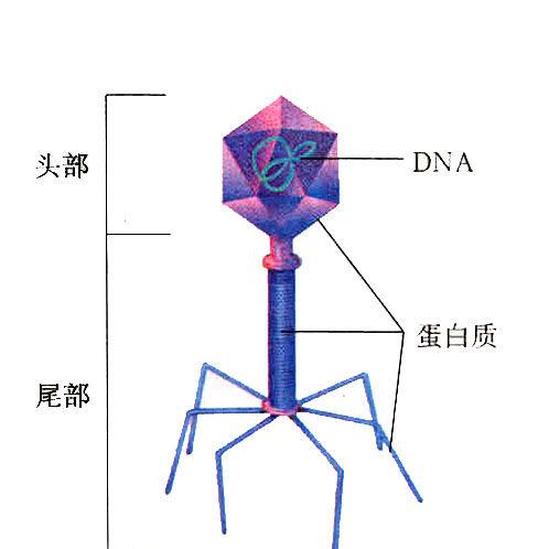初期:1915年-1940年
1915年,弗德里克· 特沃特(Frederick W.Twort)担任伦敦布朗研究所所长。特沃特在研究中力图寻找用于天花疫苗的痘苗病毒(vaccina virus)的变异株(variant),这种变异株可能在活细胞外介质中复制。他在一项试验中将一部分天花疫苗接种给一个含营养琼脂的培养盘。虽然这种病毒未能复制,但是细菌污染物在琼脂盘中生长很快。特沃特继续进行他的培养并注意到,一些细菌菌落显示出“带水的样子”(即变得比较透明)。这样的菌落做进一步培养时也不再能复制(即细菌被杀死)。特沃特把这种现象称为透明转化(glassy transformation)。他接着证明用透明转化原理感染一个正常的细菌菌落会把这种细菌杀死。这种透明实体很容易通过一个陶瓷过滤器,可被稀释一百万倍,当放在新鲜细菌上的时候就会恢复它的实力,或者说滴度。 特沃特发表了一篇描述这种现象的短文,认为对他所观察的结果的解释是存在一种细菌病毒。由于服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特沃特的研究中断了。返回伦敦后,他没有继续进行这项研究因此在这个领域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与此同时,加拿大医学细菌学家费利克斯· 德赫雷尔(Felix d’Herelle)当时正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工作。1915年8 月,法国的一个骑兵中队驻扎在巴黎郊外的梅宗-勒菲特(Maisons-Lafitte),一场严重的志贺氏杆菌引发的痢疾对整个部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德赫雷尔对患者的粪便进行过滤,很快从过滤的乳状液中分离出痢疾杆菌,并且加以培养。细菌不断生长,复盖了培养皿的表面。德赫雷尔偶然观察到清楚的圆点,上面没有长出任何细菌。他把这些东西称为乳样斑(taches vierges),或称为噬斑(plaques)。德赫雷尔跟踪观察一名患者的整个感染过程,观察何时细菌最多,斑点何时出现。有意思的是,患者的病情在感染后的第四天开始好转。 德赫雷尔把这些病毒(virus)称为噬菌体(bateriophage),紧接着他发明了病毒学研究领域的方法。他将噬斑进行有限的稀释,测定病毒的浓度。他的推论是出现斑点表明病毒为颗粒或称为小体(corpuscular)。德赫雷尔在研究中还证明病毒感染的第一步是病原体附着(吸附)宿主细胞。他通过把病毒与宿主细胞混合后共沉淀证明了这一点。(他还证明,上清中不存在这种病毒)一种病毒的附着只是在细菌对与它混合的病毒敏感时才出现,这表明了一种病毒对宿主细胞的吸附有特定的范围。他还用很清楚的现代术语描述了细胞溶菌(lysis)的释放。德赫雷尔在许多方面是现代病毒学原理的创始人之一。 到1921 年,越来越多的溶原性菌株(lysogenic bacterial strain) 被分离,在一些实验中已经不可能把病毒与它的宿主分开。这使布鲁塞尔巴斯德研究所的朱勒斯· 博尔德特(Jules Bordet)认为,德赫雷尔描述的传染性病原体只不过是一种促进自身繁殖的细菌酶(bacterial enzyme)。虽然这是一种错误的结论,但是它相当接近于朊病毒(prion)结构和复制的看法。 在20 世纪20-30 年代,德赫雷尔重点探索他的研究成果在医学上的应用,但是毫无成果。当时进行的基础研究常常受该领域个别科学家的强烈个性所产生的解释的影响。显然有许多不同的噬菌体,一些为溶菌性(lytic)而另一些则是溶原性(lysogenic),但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仍然定义不明确。这个时期的重要发现是马克斯· 施莱辛格,他证明纯化的噬菌体最大直径(linear dimension)0.1 微米,质量大约4x10克,它们由蛋白质和DNA 构成,比例大体上相等。1936 年那时没有任何人清楚地知道如何利用这种观察结果,但是,它在随后的20 年里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代:1938 年-1970 年
马克斯· 德尔布吕克(Max Delbruck)是吉廷根大学(Gittinge)培养出来的物理学家。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柏林威廉化学研究所,在那里他与一些研究人员积极地讨论量子物理与遗传学的关系。德尔布吕克对这个领域的兴趣使他发明了一种基因的量子机械模型(guantum mechanical model of gene)。1937 年,他申请并获得了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习的奖学金。一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他就开始与另一位研究员埃默里· 埃利斯(Emory Ellis)合作。埃利斯当时正在研究一组噬菌体-T2 、T4 、T6(T-偶数噬菌体)。德尔布吕克很快认识到这些病毒适合研究病毒复制。这些噬菌体是探索遗传信息如何决定一种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的一个途径。从一开始,这些病毒就被视为了解癌症病毒,甚至了解精子如何使卵子受精并发育为一种新生物体的典型系统。埃利克和德尔布吕克设计出一步生长曲线试验。在这项试验中,一种受感染的细菌经过半个小时的潜伏期(latent period)或称为隐蔽期(eclipse period)之后释放了大量噬菌体。这项试验给潜伏期下了定义,即病毒失去传染性的时候。这成为这个噬菌体研究小组的试验范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尔布吕克留在美国(在范德比尔特大学),见到了意大利难民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E . Luria)。卢里亚逃到美国避难,当时在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T1和T2噬菌体。他们是1940 年12 月28 日在费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见面的,并在随后的两天里策划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试验。两位科学家将招聘和领导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重点研究利用细菌病毒作为了解生命进程的一个模型。对他们的成功起关键作用的是1941 年夏天他们应邀到冷泉港实验室做试验。就这样一位德国物理学家和一位意大利遗传学家在二战期间一直进行合作,周游美国招聘新一代的生物学家,后来这些人被称为噬菌体研究小组。 此后不久,新泽西州普林斯顿RCA 实验室的电子显微学家汤姆· 安德森(Tom Anderson)见到了德尔布吕克。到1942 年3 月,他们第一次获得了噬菌体的清晰照片。大约同时,这些噬菌体变异株第一次被分离和鉴定。到1946 年,冷泉港实验室开设了第一门噬菌体课程,1947 年3 月,第一次噬菌体会议有8 人出席。分子生物学就是从这些缓慢的开端中发展起来的。这门科学的重点是研究细菌宿主及其病毒。
随后的25 年(1950 年至1975 年)是用噬菌体进行病毒学研究硕果累累的时期。数百名病毒学家发表了数千篇论文,主要涉及三个领域:(a)用T-偶数噬菌体进行的大肠杆菌溶菌性感染研究;(b)利用λ噬菌体进行的溶原性研究,以及(c)几种独特噬菌体的复制和特性研究,例如ФX174 (单链环状DNA)、RNA 噬菌体、T7 等。它们为现代分子病毒学和生物学奠定了基础。本文不可能一一介绍所有这些科学文献,只能提及一些有选择的重点。 到1947年至1948年,用生物化学方法研究噬菌体感染细胞在潜伏期发生的变化开始盛行。西摩·科恩(Seymour Cohen)最初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与欧文· 查格夫(Erwin Chargaff)一道研究脂质和核酸,随后又与温德尔· 斯坦利研究烟草花叶病毒RNA ,1946年在冷泉港实验室主修德尔布吕克的噬菌体课程。他利用比色法(colorimetric analisis)研究被噬菌体感染的细胞中DNA 和RNA 水平的影响。
这些研究表明,被噬菌体感染的细胞中大分子合成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a)RNA 的净积累在这些细胞中停止。[后来,这成为发现多种RNA 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证明了信使RNA 的存在]。(b)DNA 合成停止了7 分钟,随后又以5 倍至10 倍的速度恢复DNA 合成。(c)与此同时,蒙诺德(Monod)和沃尔曼(Wollman)的研究表明,噬菌体感染后一种细胞酶——可诱导β-半乳糖苷酶(galactosidase)的合成受到抑制。这些试验把病毒的潜伏期分为初期(在DNA 合成之前)和晚期两个阶段。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病毒可能改变受感染细胞的大分子合成过程。 到1952 年底,两项试验对这个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赫尔希和蔡斯利用标记病毒蛋白(SO)和核酸(PO)跟踪噬菌体对细菌的附着。他们能用搅拌机去除病毒的蛋白质衣壳,只保留与受感染细胞有联系的DNA 。这使他们能够证明这种DNA 具有再生大量新病毒所需的全部信息。赫尔希-蔡斯的试验和沃森与克里克一年后阐述的新DNA 结构共同构成了分子生物学革命的奠基石。 病毒学领域的第二项试验是1953年由怀亚特(G.R.Wyatt)和科恩(S.S.Cohen)进行的。他们在研究T-偶数噬菌体时发现一个新的碱基,即5‘羟甲基胞嘧啶(hydroxymethylcytosine)。这个新发现的碱基似乎取代了细菌DNA 中的胞嘧啶(cytosine)。这使科学家们开始对细菌和受噬菌体感染的细胞中DNA 的合成进行了长达10 年的研究。最关键的研究表明,病毒把遗传信息引入受感染的细胞中。到1964 年,马修斯(Mathews)等人的研究证明,未受感染的细胞中不存在5‘羟甲基胞嘧啶,并且必须由病毒为之编码。这些试验提出了脱氧嘧啶(deoxypyrimidine)生物合成和DNA 复制方面的早期酶学概念,提供的明确的生物化学证据表明可以编码一种新的信息并在受感染的细胞中表达。对这些噬菌体的详细遗传分析后确认了编码这些噬菌体蛋白质的基因,并绘制了基因图使概念更完整。实际上,对T-偶数噬菌体的rⅡ 和B 顺反子(cistron)的遗传分析成为研究最充分的“遗传精细结构”之一。利用噬菌体变异株和提取物体外复制病毒DNA ,对我们当代了解DNA 如何自我复制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通过对噬菌体装配的详细遗传学分析,利用噬菌体突变株体外装配的互补性阐明了有机体如何利用自我装配的原理构建复杂结构。对噬菌体溶菌酶的遗传和生物化学分析有助于阐述突变的分子性质,噬菌体突变(琥珀突变)提供了在分子水平研究第二位点抑制突变(second-site suppressor mutation)的明确方式 。DNA的环形排列、末尾冗余(引起噬菌体杂合体)结构可以解释T 偶数噬菌体的环形遗传图。 病毒和细胞蛋白质的合成在受噬菌体感染的细胞中发生明显变化,这一点是在早期研究中使用十二烷基硫酸钠一聚丙烯酰胺凝胶(sodium dodecyl sulfate (SDS)-polyacrylamide gels)而被戏剧性地发现,结果表明病毒蛋白质的合成有特定顺序,分为早期蛋白质和晚期蛋白质。这种一过性的基本调节机制最终发现了调节RNA 聚合酶和授予基因特殊性的∑因子。几乎每一个级别的基因调节(转录、RNA 稳定性、蛋白合成、蛋白处理)的研究均是通过对噬菌体感染性研究得出的原始数据揭示的。 虽然溶菌噬菌体(lytic phage)研究取得如此显着的进展,但是仍然没有人能清楚地解释溶源性噬菌体(lysogenic phage)。这种局面在1949年发生了变化,当时,巴斯德研究所的安德烈·勒沃夫(Andre Lwoff) 开始对Bacillus megaterium 及其溶源性噬菌体进行研究。通过使用一种显微操纵器将单一细菌分割多达19次,从未释放出任何病毒。当从外部对溶源性细菌进行溶解时,也没有发现病毒。但是经常出现一个细菌自发地发生溶解并释放出许多病毒来的现象。紫外线能诱使这些病毒释放是一项重要的发现,这种观察可以概述一种病毒与其宿主之间的奇妙关系。到1954年,巴斯德研究所的雅各布(Jacob)和沃尔曼(Wollman)得出重要的研究结果,即一种溶源性菌株(Hfr ,λ)与非溶源性受体在结合之后的遗传杂交(genetic cross)导致病毒的诱发。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合子诱导(zygotic induction)。事实上溶源性噬菌体或称原噬菌体(prophage)在其宿主大肠杆菌的染色体中的位置,可在遗传杂交之后用标准的中断交尾实验绘图。这是在概念上了解溶源性病毒的最关键试验之一,理由如下:(a)病毒的行为就像一种细菌的染色体上的细菌基因一样;(b)它表明病毒遗传物质由于负面的调节而在病毒中保持静止的试验结果之一。当染色体从溶源性供体细菌传递到非溶源性受体宿主时,该病毒遗传物质丢失;(c)这有助于解释雅各布和沃尔曼早在1954 年就认识到的酶合成以及噬菌体生成的诱导是同一现象的表现”。这些试验为操纵子模型(operon model)和协同基因调控(coordinate gene regulation)的性质奠定了基础。 虽然在1953年阐述了DNA的结构,1954年描述了合子诱导,但是溶源现象中细菌染色体与病毒染色体之间的关系仍被称为附着部位(attachment site),当时也只能从这些角度考虑。后来,坎贝尔(Campbell)根据噬菌体标记的顺序在整合状态下不同于复制或生长状态这一事实,提出DNA与细菌染色体进行λ整合的模型,至此,病毒与其宿主之间的真正密切关系才得到认识。这导致分离出λ噬菌体的负调节基因或称抑制基因,这是对溶原菌免疫特性的清楚了解,也是对基因如何进行协同调节的早期范例之一。对λ噬菌体生命周期的遗传分析是微生物遗传学领域的重大学术探险。它值得所有分子病毒学和生物学学者进行详细的研究。 诸如鼠伤寒沙门氏菌(Salmonella typhimurium)P22 这样的溶源性噬菌体是一般性转导(transduction)的第一个例证,而λ噬菌体是特殊转导的第一个例证。病毒可能携带细胞基因,并把这样的基因从一个细胞转移到另一个细胞,这不仅提供了精确遗传绘图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病毒学中的一个新概念。随着细菌的遗传因素被更详细地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溶源性噬菌体研究发展到附加体(episome)、转座子(transposon)、反转录转座子(retrotranspon)、插入元件(insertion element)、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嗜肝DNA病毒(hepadnovirus)、类病毒(viroid)、拟病毒(virusoid,又称类病毒viroid-like指一类包裹在植物病毒颗粒中的病毒,译者注),以及朊病毒(prion)研究,这一切使得遗传信息在病毒与其宿主之间的定义和分类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从噬菌体研究中得出的遗传和生化概念使病毒学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溶菌和溶源性噬菌体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常常随着对动物病毒的研究而被人们重新学习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