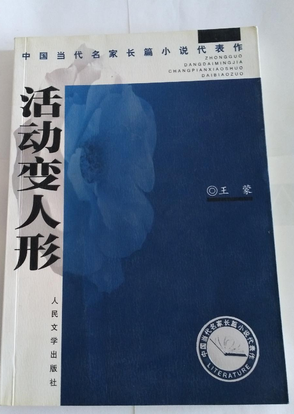主题思想
在“变”的世界:对民族文化的反省和对民族生命力的热切呼唤
《活动变人形》表面叙述的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斗争的故事,这场斗争是如此惨痛,以至于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该小说中人物的纠纷,固然有其经济的原因、性格的原因,但纷争的背后折射的深层问题却是文化的冲突。活动变人形玩具,是倪吾诚在当铺当掉了他的瑞士表给孩子买的礼物。当时他先买了鱼肝油,后买了这一礼物。这两种礼物分别代表倪吾诚在孩子身上所寄予的两种期望。他希望鱼肝油能使孩子们变得身体健壮起来,活动变人形则能够丰富孩子们的精神生活。故活动变人形这一文化符码,首先代表一种更为先进的、更具智慧的现代文明生活。该小说中倪吾诚多次慨叹中国人童年生活的贫乏,“男孩子只能拨拉着自己的小东西玩”。所以倪吾诚在为孩子们买下了这样一个代表“东洋人的先进和智慧”的玩具后,希望他们也能够享受到像发达的西洋或者东洋的孩子一样的文明生活。而且该小说中,在描写活动变人形时多次使用了“色彩鲜艳”“五彩绚丽”“五颜六色”这样一些修饰词。这样一些词汇寓指这一玩具所代表一个绚丽多彩、五彩斑斓的世界,与孩子们生活的单调、乏味的现实世界截然不同。而倪吾诚一生的向往和追求,就是他和孩子们,更确切地说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拥有、享受到的这种现代文明和智慧。所以倪吾诚宁肯当掉自己的瑞士手表,去给孩子买鱼肝油和活动变人形,表明了他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执著的态度,并且“他希望他也相信下一代能将生活得更加文明、高尚、善良、幸福。起码他们应该生活得更加健康和合理”。但除了指向一种更先进、更富智慧的现代文明的内涵外,活动变人形这一文化符码,从更深的层面上来看,还蕴涵着“变的哲学”的内涵。 该小说在解释活动变人形这一玩具的玩法时,多次提到它的头、身体、腿的部位的自由组合和变化自如:这一段关于活动变人形的描写,表面看来是对这一玩具的玩法以及其奇妙处的赞叹与欣赏,而实际上则寓意深远。活动变人形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变化,通过头、身子、腿、衣服以及人体姿态的自由组合,像魔方一样可以有千变万化的组合,从而不断地变换出各种各样的人。因而,它在深层意义上指向了一个关于“变”的辩证法的思维观。因而在《活动变人形》中,通过活动变人形这一文化符码,王蒙阐明了“变”的哲学观,即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会永远处于纯粹之中,而是必然要和其他文化相互融合、相互补充,除旧纳新,不断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固然有着五千年灿烂的独特的文明,但也背负上了沉重的封建文化的负荷,在向现代化转型期间,必须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吸纳世界其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合理内核。 但是,在《活动变人形》中,却看到了坚决抵制现代文明,固守中国封建文化的保守派。他们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捍卫者,身上残留着许多封建文化的痼疾,对现代文明、西方文化则持一种反感、排斥、厌恶甚至坚决抵制的态度。他们的行为举止、价值观念都趋向于封闭、保守的文化心态,与活动变人形这一文化符码所指向的“变”的哲学精神背道而驰。
该小说中提到的倪吾诚身边的亲人、亲戚几乎都是这一类型的人。譬如倪吾诚的母亲,在察觉倪吾诚迷恋现代先进文化后,曾一度试图用鸦片和“乱性”麻痹他的身心,以达到让他远离现代文明的目的。倪吾诚的舅父和表哥等,同样过着一种典型的蒙昧、落后的封建土财主生活——抽大烟、娶小老婆、斗纸牌、提笼养鸟、随地吐痰。倪吾诚的岳母同样坚决捍卫她随地吐痰的正确性,此事引发了她与倪吾诚之间的第一次矛盾。在倪吾诚看来,随地吐痰一种极不卫生、极不文明的行为,而倪吾诚与姜赵氏的这次冲突最终以姜赵氏的“掼茶壶”和倪吾诚的下跪求饶告终。但经历这次事件之后,倪吾诚对姜赵氏所践行的这样一种落后的、不文明的生活方式深恶痛绝:“他对这里的诸种肮脏、龌龊、野蛮和恶劣的痛恨增强了许多倍。他对之的抨击增加了许多一本《活动变人形》帮助倪藻认识到,人是由五颜六色的三部分组成:戴帽子的或者不戴帽子或者戴与不戴头巾之类的玩艺儿的脑袋,穿着衣服的身子,第三就是穿裤子或穿裙子的以及穿靴子或者鞋子或者木屐的腿脚。而这三部分是活动可变的。比如一个戴着斗笠的女孩儿,她的身体可以是穿西服的胖子,也可以是穿和服的瘦子,也可以是穿皮夹克的侧扭身子。然后是腿,可以穿灯笼裤,可以是长袍的下半截,可以是半截裤腿,露着小腿和脚丫子,也可以穿着大草鞋。这样,同一个脑袋可以变成许多人。同一个身子也可以具有好多样脑袋和好多样腿。原来人的千变万化、多种多样就是这样发生的。哎,如果每个人都能自己给自己换一换就好了。 该小说还详细描写了姜赵氏的无事乱翻东西、捣鼓煤球炉、修脚以及刷尿壶的种种怪癖,这实际上是落后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沉荷在她身上的积淀。静珍既是封建文化的可怜的牺牲品,又是这种文化的一个坚决捍卫者。她年纪轻轻就守寡,立志终身不嫁,对倪吾诚建议她再嫁深表愤恨,认为这是对自己守志的莫大侮辱。她一生一直生活在一个绝对封闭的自我世界中,心灵受到极大的扭曲,她每天梳洗得“早课”,都是个性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中的一种变态的反映。静宜同样也是一个心态守旧、封闭的封建旧文化的维护者,因而与处处以西学为生活信条和行动方式的倪吾诚处于矛盾、冲突中。“他和静宜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他讲英美,她认为全是狗屁”,“每当他讲英文,静宜总觉得比听野猫叫还可厌和晦气。他的外文使她反胃。而每当静宜唱戏的时候,他的嘴也撇得吓人”。静宜虔诚地信奉封建文化的种种规矩、信条,她极端封闭的心态在与倪吾诚“刮泥疙瘩”的冲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她的眼中,这些泥疙瘩是元宝的象征,所以她极力反对倪吾诚铲掉它们。这在接受了现代文明科学、卫生观念洗礼的倪吾诚看来,“简直是神经病。简直是妄想狂。”于是“此后再也不想触犯众多的小元宝。吃饭的时候,就把许多高贵的欧洲文明的篇章,堆放在小元宝上”,分别代表东西方文化的“小元宝”和“许多高贵的欧洲文明”就这样被奇妙、荒诞地并置于一起。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王蒙对固守封建文化、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缺乏变通文化心理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抨击。他希望人们都能像那灵活自如、自由变幻的活动变人形那样,具有变通的思想,开放的心态。
但每个人究竟应该怎样“给自己换一换?”该小说中的倪吾诚转换得最彻底,完全着上了西洋人的行头,成了一个西洋化的“活动变人形”。与静宜等固守封建文化所截然不同的是,倪吾诚走了一条全盘西化的路子。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文化的迷恋者。由于从小上洋学堂,接受了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宣扬的先进思想,对中国封建文化中“缠足”的野蛮,“拜祖宗牌位”等愚昧事宜深恶痛绝,并采取了种种极端行为向其发起挑战。及至在欧洲留学接受了欧风美雨的熏陶,他对西方文化的崇尚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应该说,他推崇现代西方文化的文明、科学、个性幸福等价值理念,是应该得到肯定的,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失的亟须借鉴的文化资源。“他是那么样希望幸福、希望高尚和文明”,尽管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有限,“但他总是怀着近乎贪婪的热情倾听别人谈科学”;他更渴望一种现代爱情,在静宜生下倪萍后,他认为他和静宜的婚姻同样是“没有任何的爱情也没有任何的文明。他像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那样坚持不懈同一切愚昧落后的封建文化作斗争,并通过洗澡、喝咖啡、吃鱼肝油,买温度计、童话书等行为践行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 然而在该小说中,倪吾诚完全变成了一个西洋化的“活动变人形”,一个彻头彻尾的“香蕉人”。他这种向西方文化一边倒的转换,该小说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只是有的三样放在一起很和谐,有的三样放在一起有点生硬,有点不合模子,甚至有的三样放在一起觉得可笑或者可厌,甚至叫人觉得可怕罢了。”可以说倪吾诚在接受了西方文化进行了转换之后,变成了一个上文所提到的“生硬的”“不合模子的”“甚至可笑”“可厌”的活动变人形。他对西方文化以及现代文明的接受可以说是囫囵吞栆,食而不化。因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对现实没有清醒认识,全盘接受并盲目生搬硬套西方文化的可笑又可怜的“香蕉人”。在倪吾诚的眼中,西方的东西就是先进的、文明的、高贵的:“欧洲,欧洲,‘我’怎能不服膺你。只看看你们的服装,你们的身体,你们的面容和化妆品。你们的鞋子和走路(更不必说跳舞了)的姿态,你们的社交和风习。”对他来说:“接近外国字母也是快乐和骄傲的”,“一想到欧洲人,一想到欧洲国家的语言,一想到诸种难懂得的名词,一想到永远清洁高贵的一尘不染的史福冈的西服和大衣,他就觉得快乐、升华,升仙”。倪吾诚对西方文化达到了一种顶礼膜拜的程度,对西方文化缺乏任何理性批判意识,甚至认为欧洲爆发的两次灭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也是值得称道的:“即使战争席卷到了那里,法西斯主义正在吞噬一切,然而那里毕竟有热烈的活人。”至此,倪吾诚对东方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肯定已走向了一个彻底的极端。 倪吾诚由抗争到失败,由追求到绝望的悲抢历程,几乎概括了近百年来在“历史的夹缝”中无所适从,委曲求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可悲可泣的命运史。然而命运感并非专指知识人而言,在一种由来已久、积垢弥深的文化魔圈里,多数人都不配有较为体面一些的人生过程。姜赵氏、静珍静宜“吃人”,也“被吃”,并且“自吃”。她们的存在,是别人的地狱,但她们自己首先是居于地狱的最底层。她们的落后、愚昧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来自于既定的传统惰力。由于跳不出祖宗遗留给他们的卑质的文化系统,缺乏参照系,无法反省自我及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可以说,她们的猥劣人生,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宿命的安排。
只有在倪吾诚的儿子倪藻身上,这种转换才达到了一种和谐的状态。与父亲倪吾诚一样,倪藻也生长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很大的影响。倪藻能以辩证的眼光清醒地看待中西文化及其关系。而不再是一个“不合模子”的人,可以说倪藻是对其父的继承与超越。
《活动变人形》的开头即以语言学副教授倪藻作为中国学者访问欧洲某著名港口城市H市参加学术活动拉开了这部小说的序幕,它从倪藻的出国写起是很有意味和构思的巧妙性的。正如该小说中所写道:“这就是‘出国’,它似乎给你一个机会超脱地飘然地返顾,鸟瞰你自己、你的历史和你的国家。”该小说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叙述了倪藻在国外的种种感受。倪藻在欧洲H市几天的访问、旅行,使他在“走到世界,来到外国后”处处以一种比较、审视的眼光对中国和欧洲的情况一一做对比分析。这是一种自觉的中西文化比较意识。一方面,倪藻对中国依然在世界处于落后地位,某些中国人文明素质较差因而被欧洲人所瞧不起的事实感到忧愤,他慨叹:“‘我们’的堂堂的中国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另一方面,他在异域父亲好友史福冈的家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致远斋”匾,“守身如执玉”和“积善胜遗金”的对联,“忍为高”的字幅、齐白石的溪水画和兰花,郑板桥的“难得糊涂”的拓片等,上述种种符码都指向中国传统文化。该小说借史福冈太太的一番话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和推崇:“史先生整天跟‘我’研究这个,他佩服中国,他佩服中国文化,他说这是全世界头一份的,谁也比不了的文化,它有它的道理。”在史福冈夫妇这一对坚定的中国文化的信仰者和维护者身上倪藻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作者通过活动变人形这一文化符码阐释了“变”的辩证法,犀利剖析、批判了以静宜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面对现代文明所折射出的封闭、缺乏变通的封建文化心态,同时,对倪吾诚缺乏理性批判态度地全盘接受并生搬硬套西方文化给予了善意、辛辣的讽刺。
《活动变人形》用历历如绘的生活画面、用活生生血淋淋的人生悲剧,对一种不人道的旧文化作了痛切的针砭。作者从自己的记忆中,抖腾出“倪象的旧故事”,令人触目惊心地展现出这一既可以作为封建社会的细胞、封建文化的缩影,但又楔入了异质文化因子的特殊的旧家庭内部发生的生死冲突,并通过描写旧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观念的承载者、维护者——姜氏母女对于新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意志的本能恐惧与拼死拒斥,以及作为旧生活旧文化的叛逝者——倪吾诚在一种先验存在的无可摆脱的文化环境中四面碰壁、焦头烂额、无计可施、无路可逃,最终为他所极其痛恶、极力抨击、呕欲挣脱的愚昧、野蛮的文化力量所吞噬、所虐杀,拯救者为被救者所掣肘,在黑暗惨苦的精神地狱里一同沉沦,成为文化传统的殉葬品、受害人,抨击了这种文化扭曲人性、压抑民族生命力和创造性的严熏罪恶。作为历尽世事沉浮、人生坎坷的作家,王蒙的审美意识并没有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的激情批判上,而是在个人命运与历史文化,人生实现与文学实现这一张力场中,骚动起多种器乐多个声部,歌奏出一支夺人心魄的命运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