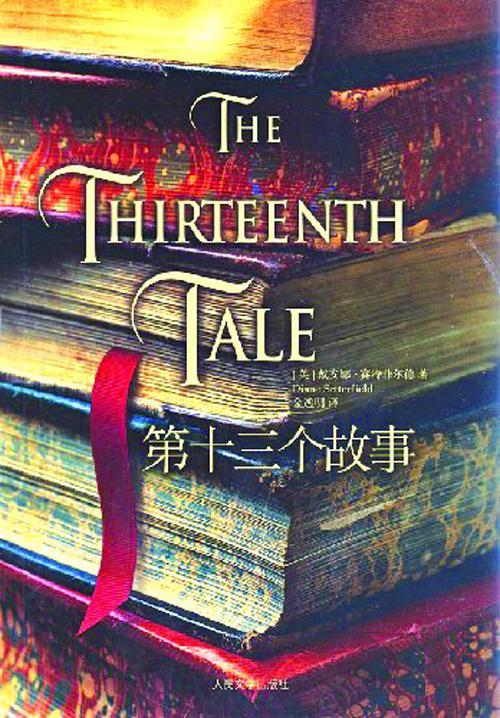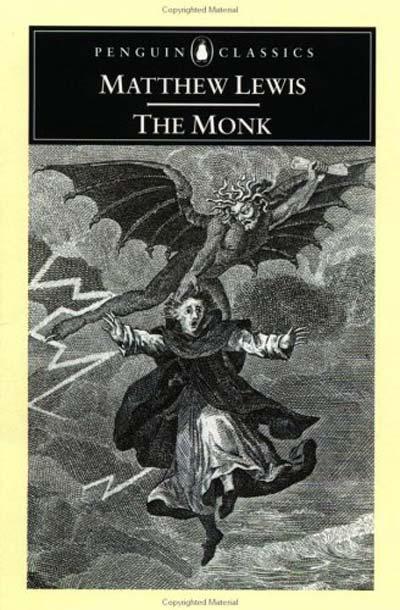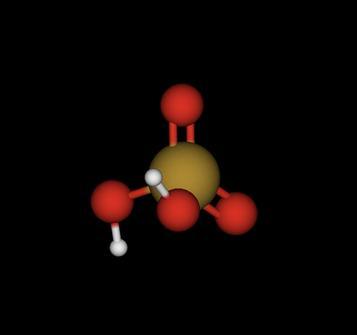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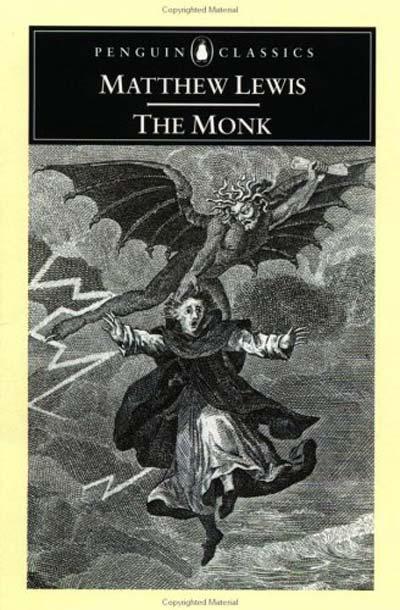
哥特式小说
不过,人们注意到当今西方的哥特式小说批评兴盛的同时,也注意到“哥特式小说”这一概念阐述的驳杂和淆乱。有的学者把它解读为一种心理宣示,是所谓社会动荡时期人的恐惧意识,特别是女性恐惧意识的自然流露①;也有的学者把它剖析为一种性欲望的掩饰,反映了作者自身的乱伦、同性恋、性受虐狂等扭曲情结②;还有的学者把它定义为一种政治颠覆,展示了广大中产阶级受众对独裁统治者、极端教会势力以及其他专制阶层人士的愤懑和抨击③;甚至还有的学者,认为它同其他商业小说一样,主要表现为一种娱乐方式,“大多数作者的主要动机是享文学创作之乐”,而读者也通过作品中的似是而非的悖论获得“恐怖的乐趣”(Nortonxi)。然而,无论是“心理派”学者的阐述,还是“性学派”学者的诠释,也无论是“社会派”学者的规定,还是“娱乐派”学者的解读,均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文本类型上,把哥特式小说视为一个跨时空、跨国界的开放系统。在他们看来,哥特式小说并非历史上一种固定的小说类型,而是自18世纪以来的一种泛恐怖小说形式。这种小说形式一直延续至今,不仅包括历史上已经获得公认的哥特式小说,还包括19世纪和20世纪的灵异小说、恐怖小说,甚至部分恐怖性经典小说。故哥特式小说作家也不仅有霍勒斯·沃波尔、安·拉德克利夫、马修·刘易斯等人,还有拉·法努(Le Fanu,1814-1873)、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1847-1912)、阿瑟·梅琴(Arthur Machen,1863-1974)、安妮·赖斯(Anne Rice,1941-)、斯蒂芬·金(Stephen King,1947-),甚至沃尔特·司各特、爱伦·坡、查尔斯·狄更斯、勃朗特姐妹、托马斯·哈代、罗伯特·史蒂文森、奥斯卡·王尔德、约瑟夫·康拉德、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托尼·莫里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等。 
哥特式
二
哥特式小说究竟是历史上一种固定的小说类型,还是自18世纪起一直延续至今,并囊括现当代灵异小说、恐怖小说,甚至恐怖性经典小说在内的一种泛恐怖小说形式?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判明历史上哥特式小说的类型本质以及这种类型本质是否在后来的那些小说当中获得延续。现代类型理论告诉我们,文本类型产生于一系列反复出现的、与作品的内容形式有关的结构要素(Miller67-78)。表面上看,历史上的哥特式小说与后来的灵异小说、恐怖小说以及恐怖性经典小说,都含有某种“恐怖”成分,而且这种“恐怖”成分也与它们各自结构要素的“质”的规定性不可分割,因而完全可以归属同一小说类型。但其实,这种观点包含着很大的片面性。
首先,历史上的哥特式小说的结构要素并不仅仅是“恐怖”。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宣告了西方第一部哥特式小说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这类小说创作模式的问世。哥特式小说的创作模式,正如霍勒斯·沃波尔在此书再版序言中所说,是“两类传奇的融合,亦即古代传奇和现代传奇的融合”(Walpole8),具体表现为故事场景、人物范式、主题意识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尤其是作为故事场景的“哥特式古堡”,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既代表18世纪英国社会的哥特式建筑的复兴潮流,又体现了当时作为“理性主义”对立面的政治观念、思想潮流和文化价值,因而是该类小说不可或缺的标志性因素。当年霍勒斯·沃波尔之所以在《奥特兰托城堡》的副标题中加上“哥特式”这个词,其因在此。也正因为这样,在此之后问世的哥特式小说作品,如约翰·艾金(John Aikin,1747-1822)和安娜·艾金(Anna Aikin,1743-1825)的《伯特兰爵士,一个片断》(Sir Bertrand,A Fragment),克拉拉·里夫(Clara Reeve,1729-1807)的《英国老男爵》(The Old English Baron),索菲亚·李(Sophia Lee,1750-1824)的《幽屋》(The Recess),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1760-1844)的《瓦赛克》(Vathek)等等均不同程度地含有这一标志性因素。后来的安·拉德克利夫,在《西西里传奇》(ASicilian Romance)、《尤道弗的神秘》(The Mysteries of Udolpho)、《意大利人》(TheItalian)等哥特式小说名篇中,更是重视“哥特式古堡”场景设置,以此为基础虚构了令人心颤的“纯真少女身陷哥特式古堡”的故事,从而将哥特式小说的艺术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极力强调“本体恐怖”的马修·刘易斯,尽管在设置《僧侣》(TheMonk)的故事场景时,已将“古堡”换为“古寺”,但“古寺”同样为中世纪建筑,也同样体现了作为“理性主义”对立面的多重价值,因而同样是“哥特式”的。 相比之下,19世纪和20世纪的灵异小说、恐怖小说以及恐怖性经典小说,其故事场景已基本从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哥特式古堡”改为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所,如司各特的《豪华卧室》(The Tapestried Chamber)里挂着旧花毯和褪色丝绸窗帘的“卧室”,拉·法努的《西拉斯大伯》(Uncle Silas)里那个长而窄、尽头有两扇高而小窗户的“暗房”,斯蒂芬·金的《宠物坟场》(The Stand)里依山靠水、绿树环绕的“坟场”等等。其中一些虽然有着“古堡”或“古宅”的名称,但也名不副实,失去了多重象征意义,如布拉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Dracula)里立在悬崖边、风景秀丽的“城堡”,詹姆斯的《螺丝在旋紧》(The Turnofthe Screw)里铺有砾石小道、遍地草绿花红的“庄园”,等等。场景更迭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增强故事的真实感,然而也正是这种“现实主义异化”,扬弃了哥特式小说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从而打破了哥特式小说的类型结构。 其次,历史上的哥特式小说的“恐怖”也不完全等同于灵异小说、恐怖小说以及恐怖性经典小说中的“恐怖”。如前所说,哥特式小说的结构模式表现为故事场景、人物范式、主题意识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其中最大亮点,除了“哥特式古堡”外,还有“超现实恐怖”。所谓“超现实恐怖”,乃是指作品中的人物受到某种形式的鬼魂、幽灵、怪兽或“不可知物”的侵扰而表现出来的害怕死亡或疯狂的高度焦虑状况。由于作品的极度夸张和渲染,读者对作品人物的这种“恐惧”感受既是“迫在眉睫”,又是“身置其中”。然而实际上,这种“恐惧”是由虚拟的“非常世界”带来的,不但不会有实际危害,反倒能让读者产生若即若离的特殊快感。“一个恐怖的场景,描写得越是荒唐、离奇、不可思议,我们就越能获得乐趣;而描写过于接近普通生活,哪怕是带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冒险经历,我们也由于缺乏出格的痛楚而不能留下记忆或思考”(Aikin119)。
安·拉德克利夫曾经在“诗歌中的超现实主义”(On the Supernaturalin Poetry)中详细分析了哥特式小说中“超现实恐怖”。她通过两个虚拟的人物的对话,指出哥特式小说实际上可以区分为“心理恐怖”和“本体恐怖”两个类型。前者以“恐惧”(terror)为目的,作品中很少或几乎不出现超现实主义的幽灵,而只是通过充满悬念的“未知物”存在,暗示可能发生的凶险,从而“扩充灵魂,使各种功能警醒到生活的高程度”;而后者以“恐怖”(horror)为目的,通过赤裸裸的超现实主义的暴力、凶杀等描述,刺激人的感官,使灵魂“凝聚、冻结,甚至湮灭”(Radcliff145-52)。安·拉德克利夫本人的《尤道弗的神秘》等作品,即是“心理恐怖”类哥特式小说的代表。她善于使用“恐惧”暗示,展示潜在的暴力威慑,其效果比用文字公开描述有过之而不及。这种“恐惧”暗示手法实际上来自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敬畏”(sublime)理论。在“论敬畏和美丽”(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中,他提出了“敬畏”也是“美丽”的,“痛苦”、“恐惧”也能带来“愉悦”的论断。而“本体恐怖”类哥特式小说的代表作家当属马修·刘易斯。在《僧侣》一书中,他不但用醒目的文字表达了与安·拉德克利夫相同的反天主教观点,还赤裸裸地展示了通奸、乱伦和谋杀,甚至连撒旦本人也充当了同性交媾的引诱者。但无论是“心理恐怖”派,还是“本体恐怖”派,都在各自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挖掘了人的潜意识、心理创伤、精神错乱、疯狂根源、禁忌、梦魇和性,揭示了社会邪恶、监狱黑幕以及贫困的兽性化效应,因而同样属于“哥特式小说”。
而19世纪和20世纪的灵异小说、恐怖小说以及恐怖性经典小说,只是部分地继承了历史上哥特式小说的“超现实恐怖”特征,两者在恐怖方式、视觉效果、社会情境、主题意识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就灵异小说来说,不但作品形式多为短、中篇,而且超现实主义的鬼魂往往成为主要描写对象。尤其是,主题通常表现为亡人的灵魂骚扰活人。这种骚扰虽能引起恐怖,但用意却未必邪恶,且往往事出有因,或为了对活人的罪孽施行报复,或为了揭露活人的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或为了宣泄对生前某种事物的留恋,或成就一项终身奢望的事业。而恐怖小说除了继承有灵异小说的若干特点之外,主要是展示“邪恶”。作品的超现实主义的亡灵,不再与“骚扰”相连,而是成为“邪恶”的根源。如布拉姆·斯托克所塑造的吸血鬼“德拉库拉”,出身异国名门,外表英俊潇洒,但作恶时显现两颗獠牙,刺入受害者体内吸食鲜血,与此同时,受害者本身也成为吸血鬼。这样的“恐怖”已经与安·拉德克利夫所说的“心理恐怖”、“本体恐怖”没有多大联系。同样,19世纪和20世纪恐怖性经典小说的“恐怖”也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安·拉德克利夫所说的“心理恐怖”和“本体恐怖”。其主要区别是,前者基本上不含超自然因素,而后者往往含有一定的超自然因素。
三
那么,能否说,哥特式小说的文本类型可以采取“狭”、“宽”两种划分,前者指历史上已经获得公认的哥特式小说,而后者泛指一切含有“恐怖”因素的小说作品?答案也是否定的。
现代类型理论不仅概括了文本类型的结构要素,还揭示了其社会历史属性。美国学者米勒(C.R.Miller)指出,任何文本类型不是静止的、孤立的,它们产生于社会,又作用于社会,是社会行动的产物。决定文本类型的,不仅有内容形式,更重要的,还有文本、“人”及其社会活动的相互作用(Miller67-78)。因此,要判明哥特式小说的类型本质,不能仅仅考察作品的内容形式,还要考察其社会功能和目的,尤其是社会接受的情境。而从历史上哥特式小说接受的社会情境来看,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哥特式小说在图书市场经历了18世纪90年代的辉煌之后即开始衰退,至1834年后逐渐销声匿迹,因而在社会接受面上存在一个明显的“断层”。也即是说,哥特式小说作为一个文本类型,在1834年后已经逐渐失去了其社会功能和目的,不可能与后来的灵异小说、恐怖小说,以及恐怖性经典小说合流。
美国学者戴维·里克特(David Richter)说:“哥特式小说作为文学史上一个场景,从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城堡》的起源、流行,到19世纪20年代初的衰亡,确实是封闭性的历史过程,因为就其类型而言,它的所有意图和目的都死亡了”(Richter.125)。戴维·里克特这里说的“衰亡”、“死亡”,主要基于20世纪早期伊迪丝·伯克黑德(Edith Birkhead)、罗伯特·梅奥(Robert Mayo)、德文德拉·瓦玛(Devendra Varma)等人的哥特式小说研究专著中的相关论断和史实。伯克黑德指出,1797年安·拉德克利夫出版《意大利人》之后,哥特式小说的声誉就渐渐断送在那些只顾赚钱、不顾艺术的人手中(Birkhead185)。罗伯特·梅奥同意伯克黑德的看法,并举出两个事例作为佐证,一是安·拉德克利夫因图书市场上哥特式小说总体声誉下降而愤然“封笔”,二是出现了哥特式小说反讽性作品,如伊顿·斯坦纳德·巴雷特(Eaton Stannard Barrett,1766-1820)的《女杰》(The Heroine),简·奥斯汀的《诺桑格修道院》(Northanger Abbey)(Mayo58-59)。德文德拉·瓦玛则认为,哥特式小说确实在1820年前几年失去了强劲的魅力,所谓流行到19世纪中期甚至更长,其实是相对少数读者而言(Varma186)。 如果说,上面引述的伊迪丝·伯克黑德、罗伯特·梅奥、德文德拉·瓦玛等人的言论还带有个人的臆测和推论,那么下面引述的60、70年代路易斯·詹姆斯(Louis James)、维克多·塞奇(Victor Sage)、科拉尔·安·豪厄尔斯(Coral Ann Howells)等人的言论则是凿凿有据了。路易斯·詹姆斯说,当时哥特式小说失去魅力是因为那些“雇佣作者”、“低等阶层作者”“没有足够的环境描写能力来制造不可知的悬念”(James80)。维克多·塞奇则进一步补充说,1820年后“哥特式小说破碎了,畅销书发生两极分化”,一面是“雷诺兹的‘廉价恐怖故事’”,另一面是“司各特的占绝对优势的文学传统”(Sage84)。而由于上述状况,豪厄尔斯说,阅读哥特式小说已经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笑柄”(Howells80)。然而,他们的论述还留有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阅读哥特式小说成为“笑柄”?哥特式小说退出历史舞台究竟是什么时候? 2005年,英国学者弗朗兹·波特(Franz Potter)出版了专著《哥特式出版书籍的历史1800-1835》(The History of Gothic Publishing1800-1835),该书以确凿的史料考证了哥特式小说的衰落及其具体时间。最后,他得出结论:“1800年至1835年这段时期意味着哥特式小说的衰落。正如上面所说的,沃尔特·司各特于1814年出版的《威弗利》是向哥特式小说读者群首次挑战的标志,而威廉·哈里森·安斯沃斯于1834年出版的《鲁克伍德》被我选作它的终点,是因为该书代表19世纪30年代感官小说的崛起”(Potter7)。 综上所述,哥特式小说不可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开放系统,而仅是文学史上一个已经逝去的文学过程。该过程始于1764年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城堡》,终于1834年安斯沃斯的感官小说《鲁克伍德》,前后历时70年。尽管在此之后,包括灵异小说和现当代恐怖小说以及部分经典小说在内的许多英国小说都承继有哥特式小说的某些要素,但它们只是在创作上受了它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哥特式小说已不复存在。当前大多数西方学者将哥特式小说“泛化”的弊病是抹杀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形式小说之间“质”的差异,造成了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从而根据错误的前提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揭示哥特式小说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同其他形式小说之间的本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