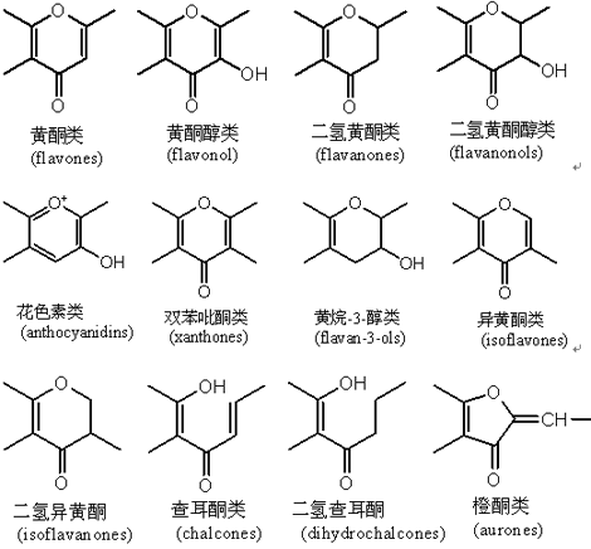作者简介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张洁,当代女作家。原籍辽宁,生于北京,读小学和中学时爱好音乐和文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翌年加入中国作协。1982年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并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国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著有作品集《张洁小说剧本选》,小说散文集《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小说集《祖母绿》,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全国第2届茅盾文学奖,曾被译成德、英,法,瑞典等多种文字出版)。
《只有一个太阳》,散文集《在那绿革地上》以及《张洁集》等。张洁获意大利1989年度“玛拉帕尔帝”国际文学奖。她的《谁生活得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分获1979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祖母绿》获全国第3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有一个青年》改编拍摄成电视剧播映,张洁以“人”和“爱”为主题的创作,常引起文坛的论争。她不断拓展艺术表现的路子,作品以浓烈的感情笔触探索人的心灵世界,细腻深挚,优雅醇美。
人物解析
主人公孙长宁是伐木工人的儿子,尽管生活在森林的怀抱中,但在“文革”年代,也不得不被烙上“伤痕”印记。只是这“伤痕”与《班主任》里谢惠敏的并不相同。如果说谢的“伤痕”属于“反文化”(排斥优秀文化),那么,孙的则是“无文化”(缺乏优秀文化)。处在远离都市文化“中心”的自然“边缘”地带,孙虽然可以躲避谢所遭受的“反文化”意识形态的直接强制,却也不得不领受“无文化”的苦痛(如无法接受正常教育,以及不懂“黑线人物”和“文艺黑线专政”等)。这同样属于由政治控制所造成的人的蒙昧状况。谢的“反文化伤痕”固然可以通过《班主任》所揭示的那种政治启蒙手段去疗救,但面对孙的“无文化伤痕”,这种手段是否仍然有效呢?或者不如进一步说,面对这两种不同“伤痕”,单一的政治启蒙手段就足以成功吗?当《班主任》等小说几乎一致倾心于政治启蒙、为我们幻化出政治启蒙的乌托邦时,《森》却独辟蹊径,亮出了诗意启蒙这一与众不同的新路。
林区少年孙长宁的无文化的蒙昧状况,由于被放逐的“黑线人物”梁启明的到来而改变了。“梁启明”这一名字本身,就透露出叙述人强烈的“启蒙”(启明)冲动。不过,这位音乐家无需像“班主任”张俊石对待谢惠敏那样从事政治灌输,而是借助音乐、以诗意去开启孙长宁。“这片在生活里偶然出现的笛声,使他丢掉了孩子的蒙昧”。正是在音乐体验中,这两位带有不同“伤痕”的人的心灵,“被同一种快乐和兴奋激发着”,彼此相互沟通,竟“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年龄的差别,忘记了时间已经渐渐地过去”。从此,梁就以“代父”的姿态,借助于音乐陶冶而对孙实施全面的知识教育(包括读、写、算等)以及道德教育(如决不能把音乐才能当商品)。重要的是,不仅被启蒙者孙的蒙昧心智被开启,而且启蒙者梁自己一时间仿佛也回到快乐的孩童时代。梁终因癌症不治而逝,但他的音乐生命在孙的身上延续和光大。最后,孙凭借梁所传授的高超音乐技艺,终于在北京成功地征服了主考教授傅涛和其他考生,被破格录取为音乐学院大学生。其他考生在严酷竞争面前竟如此无私地乐于让贤,这无疑属于那时人们信仰的音乐-情感乌托邦。这些无疑有力地暗示出,音乐的魅力远比单纯政治灌输更为巨大而神奇,它可以使饱受政治创伤的人们获得心灵的解放,争得新生的权利。
艺术价值
《森》试图显示一条面对政治蒙昧的诗意启蒙之路。诗意的启蒙,简单讲来也就是审美的启蒙,即凭借对自然、艺术的审美体验而使蒙昧的心灵乃至整个生存方式获得解放。启蒙方式应是多样的,不仅有政治的启蒙,还有科学的、道德的、哲学的和诗意的启蒙等。尤其关键的是,按《森》的刻划,这些启蒙方式都应借助于诗意的方式去实现。孙长宁作为一位“文革”政治硝烟中的蒙昧的林区少年,不仅能出污泥而不染,而且令人惊异地成长为新时代音乐人才,靠的正是来自梁启明的诗意启蒙。这似乎已经表明,诗意启蒙是中国驱除政治蒙昧的理想路径。
《森》所披露的这种诗意启蒙理想,其实正是流动于80年代前期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一种普遍冲动。例如,那时弥漫人文科学领域的“美学热”正可以说明这一点。面对“文革”浩劫留下的恶果,许多人相信,单靠科学、哲学、道德等启蒙手段是不够的。必须凭借“美”或“审美”的魅力,才能使中国人抚平政治“伤痕”而获得健全的自由的生命。《森》通过梁启明对孙长宁的音乐熏染,使现实文化语境中的这种普遍而一时难以实现的强烈要求获得一种象征性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森》显示了比具体的文学意义远为广大的文化意义。或者不如说,站在90年代视界上,把《森》置入80年代文化语境中,那么它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就应比曾经获得的更高。如果把《班主任》称为80年代文学中政治启蒙的初次呐喊,那么,《森》就应是其诗意启蒙第一声。
同时代作品比较
另外,当其他“伤痕文学”本文(如《班主任》和《伤痕》等)由于难免政治说教而在今天都几乎难以阅读时,《森》却能幸免地不在此列。尽管它也有那么一点政治“套话”,但它那简朴、自然和清新的语句及其所展示的诗意启蒙胜境,至今仍能打动人们。也许,它还能打动新世纪的读者们。因为,它所显露的诗意启蒙道路,很可能仍会成为那时困扰人们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它由于富于魅力地显示了文化界诗意启蒙理想而被称为80年代短篇小说杰作,该是并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