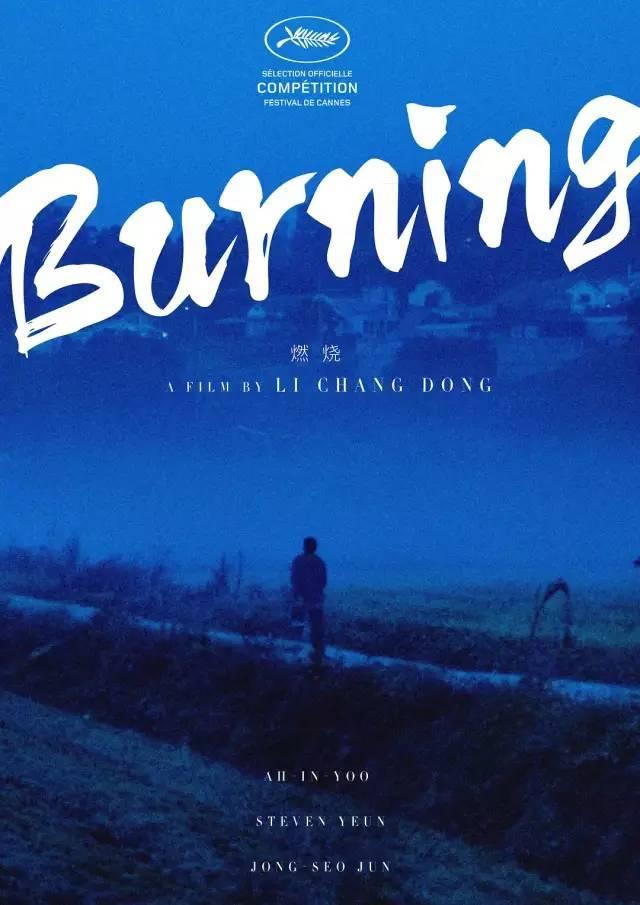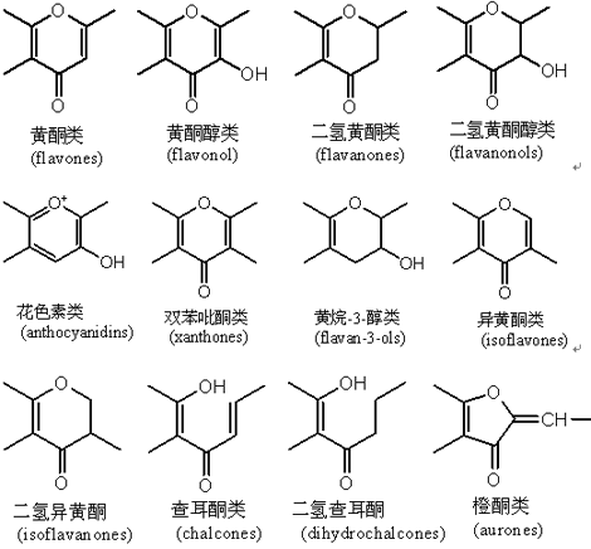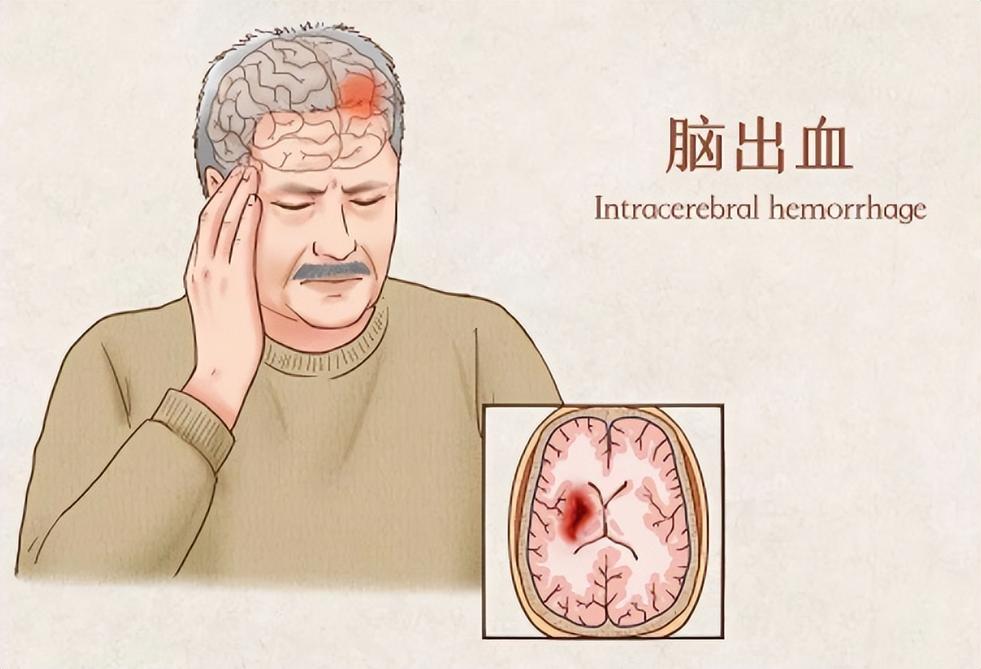作品简介
《烧马棚》讲述的是美国内战以后南方白人佃农阿伯纳·斯诺普斯一家的生活。父亲阿伯纳脾气暴躁,习惯用烧马棚的方式解决一切与邻居或雇主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当他因为与邻居哈里斯先生发生矛盾,雇人烧毁了后者的马棚而被告上法庭,他最小的儿子沙多里斯·斯诺普斯为了家庭亲情,为了父亲免于处罚,被迫出庭为父亲做伪证。然而,这个十岁的孩子本能地感觉到父亲的做法有违法规,有悖道义,他在忠实于家族血统和坚持公平正义的抉择中痛苦地挣扎着。他曾经希望父亲能从此有所改变,但是当他们与新雇主德斯潘少校发生摩擦时,父亲又一次不顾他和母亲的劝阻执意要去烧毁少校家的马棚。这是压垮沙多里斯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终于无法按捺内心的冲动,跑到少校家去报信。父亲的计划失败了,沙多里斯也无法回家面对父亲,他只能独自一人去寻找新的生活。
创作背景
1865年4月,南北战争以北方的胜利宣告结束,四年的战争使得数千万家庭流离失所,以传统农业为生的南方大地变得贫瘠不堪。战后,南方的农业生产资料被重新进行了分配,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土地集中在一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化的白人地主手里,并分租给获得人身自由的黑人奴隶和穷白人来耕作。穷人们除了基本的劳动工具之外,没有土地,不得不和白人地主签订契约,租赁少量的土地进行劳作,等到收获后再按照契约规定上交粮食给白人地主。他们没有多余的财产,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住所,作为被剥削的弱势群体,只能不断地寻找可以生存的地方,走到哪里,住在哪里。
福克纳受到南方传统的熏陶,在关于祖先的勇敢、荣誉、怜悯、骄傲、正义、自由的种种传说中长大,对家族的自豪和故土的热爱从小就在他心灵深处播下种子。然而南方的迅速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和战后美国社会“迷惘”思潮的蔓延,促使他对传统作出反思,面对现实作出新的思考,揭去南方精神遗产的美丽外衣,看到了南方奴隶制的罪恶,种植园主的腐败、残酷和非人性的一面。
角色介绍
阿伯纳阿伯纳事实上“并不是一名士兵,只能说是一名好汉”,因为他“根本不穿制服,根本不效忠于哪一个人、哪一支军队、哪一方政府,也根本不承认谁的权威”,他出现在战场上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猎取战利品——缴获敌人的也罢,自己打劫的也罢,反正在他看来都无所谓,压根儿无所谓”。但他还是和其他千千万万身处战争中的人一样,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和伤害。阿伯纳由于在战争中偷了马匹逃跑时,被子弹射中而成为终身残疾。突如其来的变故和无法接受的生理缺陷导致他心理的严重扭曲,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他对周围所有事物的强烈的不信任感,二是他对战争和与战争相关的一切人和事的深刻仇恨。
另外,战争的残酷和毁灭性激发了阿伯纳的求生本能,养成了他对火的热爱和尊重,在他看来,火就是他生存的基本,是他保护自己和反击敌人的武器,“只有靠火的力量才能保持自身的完整”。也正因为这样,每当他觉得受到冒犯和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都会放一把火来进行报复,然而此火却非彼火,这是他反抗和复仇的火,这个时候他再也不会吝惜火种,并且希望它越燃越旺,把一切都烧个干净,这样才能保持自身的尊严,“不然强撑着这口气也是白白的活着”。
阿伯纳最初并对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幻想,只是希望能够“换个农庄种一熟庄稼”,当女儿认为“这屋子只怕连猪也住不得”的时候,他劝他们“怎么住不得呢,你住着就喜欢了,包你不想再走了”。他也想让家人从此就过上安稳日子,因此才一到新的地方就想着去主人家报到,因为“从明天起人家就要做我八个月的主子了,我想我总得先去找他说句话”。他也并非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人,先不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如何东奔西突想办法赚钱,即便是战后不得不为地主家打工,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时,为了能生存下来,他也是“天边刚刚吐出火红的霞光,就已经在地里给骡子套犁了”。但是阿伯纳的努力并没有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辛苦劳动换来的是生活的日益窘迫,到最后全部家当只剩下一辆大车、一匹瘦骡、几件旧家具,全家人吃的是冷菜冷饭,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阿伯纳唯一的一件体面的黑礼服还来历不明,就是地主家的黑奴也比他们穿得整齐。在白人地主看来,阿伯纳“自出娘胎还不曾有过一百块钱”,也“永远休想有一百块钱”,这样无望的生活和一天天沉重的压力让阿伯纳看不到一点曙光。
长期的饱受压榨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逐渐使得阿伯纳内心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作为一个白人农民,在战前他可能曾一度拥有自己的土地,甚至还有一两个黑奴供差遣,此时却沦落到和曾经的黑人奴隶共同劳动的局面。他开始意识到,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自己永远不可能摆脱被欺凌的命运,而且白人地主是不会对穷人心存怜惜的。他模糊地知道地主家的财富和体面生活全是通过剥削他人劳动换来,从前是剥削黑人奴隶,可是战后蓄奴是违法的,就转而剥削自己这些穷白人。所以当他走出德·斯班少校家的大宅子时,他再也压制不了内心的怒火和不平,“那是汗水浇成的,黑鬼的汗水浇成的。也许他还嫌白得不够,不大中意呢。也许他还想浇上点白人的汗水呢”。阿伯纳内心的仇恨越积越深,但是他知道和有钱的地主比起来,他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因为“在他们的面前他只是一只嗡嗡的黄蜂,大不了把人蜇一下罢了”。
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他不得不学会保护自己,他知道牺牲自己并不能换取斗争的胜利,所以他告诫儿子,“你得学着点儿。你得学会爱惜自己的血,要不你就会落得滴血不剩,无血可流。”他内心渴望保持最起码尊严,并且想要体面地活着,所以在孩子的眼里,当他们面对地主家的大宅子时,“这雪白的门也并没有使爸爸的身影矮上三分,仿佛爸爸已经憋着一腔凶焰恶气,把身子缩得不能再缩了,说什么也不能再矮上一分一毫了。”处于这种心理状态的阿伯纳急需找到一个可以发泄的途径。但是以阿伯纳的社会地位而言,他受过教育的可能性非常小,更没有机会接受任何一种革命思想的引导,对贫富不均的认识还处于最原始的阶段,不懂什么叫阶级地位的差异,也不懂得采取其他的更为有效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和家人,通过理性的反抗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当他再也无法承受战争带来的残疾的折磨和对残酷的社会现实的仇恨时,阿伯纳的个人尊严感和他血液中天生的破坏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激发,他想到了三十年前的夜里,他赖以度过漫漫长夜的火,那是他最有力的武器,所以他选择以纵火焚烧地主家马棚的方式来实施报复,因为马棚里储存着农业社会繁衍发展所需的全部东西:劳动工具、牲口及种子,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在保护自己的同时达到打击有钱的白人地主的效果,让他们产生挫败感。
沙多里斯在福克纳的神话中,若从精神境界来划分,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 一个是沙多里斯的世界,一个是斯诺普斯的世界。在他所有成功的作品中,他都细致的发掘着这两个世界,并对这两个世界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进行戏剧化的描述。这是一场带着普遍意义的冲突。沙多里斯们按传统精神行事,也就是说,他们本着道德上的责任感行事。他们代表了有生命力的道德——人道主义。从沙多里斯的观点来看,反传统的斯诺普斯们是不道德的。但是斯诺普斯们并不承认这个观点;他们的行动只从私利出发,根本不管什么道德上的责任。因此,他们是超道德的,他们代表了自然主义或兽行。沙多里斯与斯诺普斯的冲突,实质上是一场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的冲突。沙多里斯最终并没有像哥哥一样成为一个典型的斯诺普斯家族式的人物,而是成为了沙多里斯世界中的一员。他没有服从古老的家族血统的呼唤,袒护父亲的恶行,而是选择了背叛血统,坚持正义。虽然他知道这会让他的父亲很失望。从他跑到得斯潘少校家通风报信,到他逃离他的亲人,以及他对的生活中不断反复的搬家,烧马棚和审判的循环的感到厌倦——他逃到了一个他本能的好像不仅接受而且相信其法律与规则的社会。沙多里斯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似乎厌倦了总在搬家的生活。因为搬家对于他们并非一段美好新生活的开始,他们每次搬迁都意味着要寻找新的安生之所。
因此,当他站在德斯潘少校家的大房子前,感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时,他也站在了一个新的理解世界和生活的边缘。大房子的一切,它的装饰,里面的人,它所代表的安稳舒适的生活,都让他向往。他这才知道原来人还可以这样生活,生活还可以如此安宁,如此舒坦。原来生活并不像自己的父亲和家人一样整天处于不稳定和迁徙的状态中。这座宅子让他把爸爸忘了,也把心头的恐惧和绝望全忘了,后来虽然又想起爸爸(爸爸并没有停下脚步),那恐惧和绝望的感觉却又不再了。因为,像眼前这样的一座宅第,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大得真像官邸呢——他暗暗想着,心里不觉顿时安定起来,感到一阵欣喜,爸爸惹不了他们了。生活在这样安宁而体面的世界里的人,他别想去碰一碰; 在他们的面前,他只是一只嗡嗡的黄蜂,大不了把人蛰一下罢了。这个安宁而体面的世界自有一股魔力,就算他想尽办法放上一把小小的火,这里大大小小的马棚牛棚也烧不掉一根毫毛。以至于后来他甚至想到了一种在无罪的,不惹人生气,不放火,不起诉的状态下生活的可能性,并决心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他的情感与社会道义之间的冲突。
沙多里斯在对家庭的忠诚和他自己对于公平和正义的感受的冲突中被割裂了。当他的忠诚遭到考验时,他身上“善良,正义”好的一面本性战胜了血统和家族中“邪恶,暴力”的一面。但是,怀揣正义的沙多里斯在背叛了父亲,背叛了家庭之后,除了离开家逃到他所认识的怀有敌意的,敌对的世界中别无选择。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这个世界也意味着正派,体面和规矩生活,但是没有人因为他选择了正义,背叛了父亲而接纳他,欢迎他。
故事中的小沙多里斯最终逃离了他的家庭,逃离了他所挚爱的家人,也逃离了一直折磨着他的愧疚与良知。他的未来因为他的选择变得不一样。他觉醒了,故事结尾处,他看出“天马上就要亮了,黑夜马上要过去了。他从夜莺的啼声中辨得出来,何况太阳也就要出来了。”等待他的是光明而充满希望的新生活。“暮春之夜的这颗响亮的迫切的心,正在那里急促,紧张的搏动,他连头也不回地去了。”至此,这个十岁小男孩终于完成了他从懵懂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
作品鉴赏
主题作者采用了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和全知视角,透过一个十岁孩子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带领我们进入到旧南方的世界。这种叙事手法有效地突出了父亲的形象,表达了孩子的内心矛盾。这种矛盾从本质上来说是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博弈。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基本上是外部世界的代表,而超我则作为内部世界和本我的代表与自我形成对象。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最终将反映为现实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的悬殊差别。
当沙多里斯第一次见到德斯潘的大房子和庄园时,尽管还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依然试图改变父亲,阻止父亲的暴力行为。这是一种全新的通过本能获得的道德冲动。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这个冲突让人糊涂,让人不安,让人觉着可怕。然而,从长远来看,它却可能意味着解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沙多里斯近乎福克纳心目中的英雄。他一直以来都在忍受父亲的压制,却依然能够在内心深处保留对于尊严和人性的追求。在阻止父亲烧少校家的马棚这件事情上,沙多里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被忠于血统还是忠于道义的矛盾折磨得十分痛心。虽然表面看来他决心阻止父亲是因为德斯潘少校家的房子让他觉得美好,他很想留住这份平静,但真正的原因是他内心深处自然向善的本性,他与生俱来的美好的人性。早在故事的第一幕阿伯纳被控烧毁哈里斯先生家的马棚时,他就已经有了说出事实真相的冲动。
当他的父亲因为他的这个倾向而揍他,沙多里斯依然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就是真理和正义。和父亲第一次见到德斯潘家的房子的时候,他以为脾气暴躁的阿伯纳终于会在这座大房子前却步,不去招惹他们。他多么希望父亲能够感受到房子所散发出来的安宁和体面的气息,多么希望父亲受到这种他们从未体验过的幸福生活的感染,从此改过自新,重新安排生活。“他先前干那号事,可能也是身不由己,或许这一下就可以叫他改一改了。”然而,沙多里斯错了,他的父亲仿佛“已经憋着一腔凶焰恶气”,最终还是让他不得不直面毁灭与公平的抉择。阿伯纳因为冒犯了新的雇主德斯潘少校,再次准备放火烧上校家的马棚以给这个过着舒适生活的高高在上的白人一个教训的时候,沙多里斯终于无法忍受了,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父亲再次犯错,再次打碎他心中的关于安乐家园的梦想。他做出了一个他必须做出的选择,为了道义,为了社会责任,他放弃了自己的血统。他挣脱了母亲与姨妈的看管,跑去向德斯潘报信。他的这种行为也许会直接导致他父亲的死亡,他十分清楚这种可能性。他甚至设想这一幕已经发生了,他已经开始为失去父亲而悲伤。当枪声响起,他一度认为由于自己报信导致了父亲的死亡。
弗洛伊德认为作为图腾的动物实际上是父亲的替代品,而这就很好的揭示了通常禁忌会杀死图腾动物,而这种杀戮通常又被哀悼的矛盾。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今天依然主宰着孩子们心中存在的父亲情结。也主宰了此刻沙多里斯的心情。他依然爱着,或者他尝试着去爱他的父亲,至少他愿意相信父亲至少是勇敢的,并且执拗地认为他曾经参加过战争,并且是沙多里斯上校军队中一员。“他是好样儿的”,然而他不知道父亲在战争中并不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他爸爸根本不穿制服,根本不效忠于哪一个人,哪一支军队,哪一方政府,也根本不承认谁的权威: 他的爸爸去打仗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战利品——缴获敌人的也罢,自己打劫的也罢,反正在他看来都无所谓,压根儿无所谓。
在小说《烧马棚》中,不同性质的对立面被并置在一起了:坚毅和恍惚,坚持和放弃血缘关系,有美食却得不到,一直在路上却又不得不重回起点等。这些对立面的并置充分说明了孩子内心艰难痛苦的挣扎。而火的寓意正好却是孩子为什么有这样痛苦挣扎的原因。父亲为了维护其尊严的种种行为给孩子带来了真正的痛苦。各种不同性质的对立面的并置深刻表现一个孩子要在家庭观念、血缘关系和仁义、公道、正派等处世之规的冲突中作出正确的道德抉择时何等艰难。
马尔科姆·考利曾经在他的《福克纳:约克纳帕法的故事》中援引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美国新小说家》的对话:“严格的说,福克纳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有灵魂的。”考利认为纪德的意思是,这些人物没有一个是运用自觉选择善恶的官能的。他们为某种内在的需要纠缠着,蛊惑着,驱赶着。这大概能够解释处于故事的核心位置的沙多里斯最终的选择,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说福克纳最终关心的并非这个男孩。这绝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说教的简单故事。故事的作者试图引领我们去思考另一个更为深刻的耐人寻味的主题:人类内心的古老真理以及它存在的真实性。
手法小说以在杂货店的听证会开篇,引入沙多里斯的视角,向我们介绍了杂货店和这场听证会的起因——怀疑父亲烧了哈里斯家的马棚,接着我们便随着他的所见、所感、所闻经历了这场听证会,体验了他不得不面对撒谎作证时的紧张与不安。随后我们便跟着他见证了搬家、搬家路上父子的对话、偏执暴躁的父亲和德·斯班少校家的几次交锋、以及当父亲又要烧德·斯班少校家的马棚时他面临选择正义还是忠诚时的矛盾等一系列事件。人物——聚焦者的选择在突出父亲虽坚定、不屈不挠却又暴戾、偏执、自私的性格方面更有说服力,而且不断的心理描写则让读者近距离的体验到了孩子的矛盾与挣扎。
采用人物视角必然会涉及人物的感知、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层面,因此人物视角也就透射出人物在一定叙事情境中的情感态度、价值取向等等。这篇小说也因采用人物视角,对孩子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内心观察,这些心理描写自然而又真切地传达了孩子渴望安定平静的生活却又不得不面临选择“血”还是道义时的矛盾。小说对孩子的心理描写除了两处是借叙述者的介入表达外,其他都是内部聚焦,此时我们感受到的一切都是借人物的眼光、感受、思考来获得的。第一次对孩子进行心理描写是小说开头在杂货店的听证会上:
他就是在那种绝望的心情下暗暗地想:那可是我们的仇人,是我们的!不光是他的,也是我的!他是我的爸爸啊!”
孩子不断地向自己强调那是“我们的仇人”“他是我的爸爸”,可见此时孩子内心一直在挣扎,迫使自己选择对血统对家庭的忠诚。治安官宣判他们一家要离开本地后,孩子坐在马车上,看着渐渐消失的杂货店、一大堆人,心想:
“永远看不见了。他这该满意了吧,他可不是已经……”
孩子虽然选择了忠诚于父亲,但内心对父亲的做法还是不认同的。全篇小说没有出现一个“矛盾”“挣扎”这些词,然而通过这些心理描写,却能让读者近距离地体验到孩子对父亲复杂矛盾的心情。最后当孩子告发了父亲孤独无助地躲进树林之后,突然叫出声来:
“他是好样儿的!”“好样儿的!到底打过仗!不愧是沙多里斯上校的骑马队!”
背叛父亲选择道义之后,却又自豪于父亲的勇气和魄力,此时再多的外在描述也没有他内心的一句“他是好样的”能更让人体会到矛盾之深。孩子对安定平静生活的渴望是通过两处叙述者介入的心理描写来传达的。当孩子看到德·斯班少校的宅第时,“感到一阵欣喜”,然而其中的“原因他是无法组织成言语的,他还太小,还说不上来”,这时全知叙述者跳出来告诉我们,“其实这原因就是”:
“爸爸惹不了他们了。生活在这样安宁而体面的世界里的人,他别想去碰一碰;……这个安宁而体面的世界自有一股魔力,就算他想尽办法放上一把小小的火,这里大大小小的马棚牛棚也决烧不掉一根毫毛。”
这里作者巧妙运用了儿童视角的人为视角限制(因儿童的观察力、思维力的不成熟),自然地进行了视角转换,由第三者全知叙述者道出孩子的想法:他只是想过上安宁的生活,却因为父亲暴躁偏执的性格一家人不得不颠沛流离。这里由第三者说出孩子的想法,要比直接由孩子的视角说出“爸爸惹不了他们了。我们可以在这过上安静的日子了”(一个十岁的孩子完全有能力简单地表达这种想法)更让人震撼。因其视角的转换,恰当地控制了读者与小说人物的距离,让读者同情孩子的同时,更反感父亲的自私。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和叙述者全知叙述视角的转换,取得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作者简介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美国小说家。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加拿大空军中服役,战后曾在大学肄业一年,1925年后专门从事创作。他被西方文学界视作“现代的经典作家”。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和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故事发生在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这部世系主要写该县及杰弗逊镇不同社会阶层的若干家庭几代人的故事。福克纳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