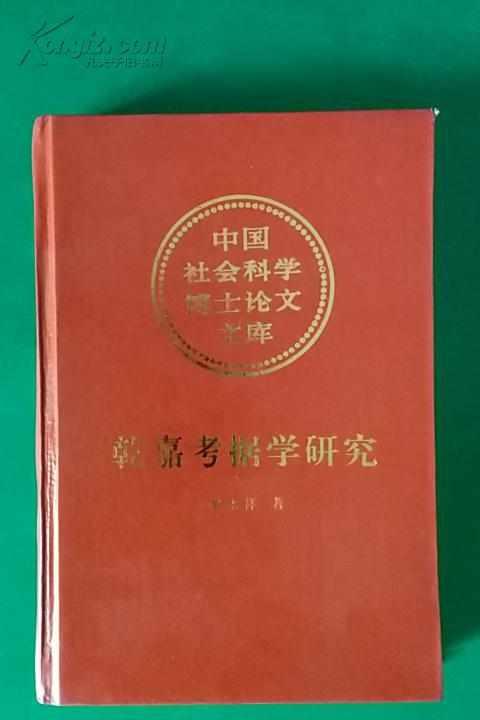定义
随着清朝统治趋于稳固,思想学术界呈现了与清初不同的变化,即考据学开始在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乾嘉考据可认为是一种学风,也可指一种方法,却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因为这个时期的学者都尊行以经学为主的汉代学术,故称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为汉学。又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朴实无华的考据功夫,故又称其为朴学。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也称之为乾嘉考据学。[1]
成因
乾嘉考据的出现和形成,有多方面原因。
从社会政治原因
清统治者征服全国后,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发展,乾嘉时期是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即所谓“乾嘉盛世”,在这种情况下,对文化有进一步的要求十分自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更是必需的。从顺治时代到康熙时代,因为统治秩序尚未稳定,清朝君主对坚持气节的明朝遗民主要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顺、康二朝文字狱与乾、嘉二朝相比要少,处罚和株连的程度也轻缓一些。只要没有明显危及统治,隐居不仕的明朝士大夫可以在他们的范围内著述、讲学,也可以不去响应为拉拢他们而特地开设的博学鸿辞科。顺、康以后,情况有所不同。已经腾出手来重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并且被充分汉化而深谙统治术的清朝帝王开始施行文化高压政策。康熙以后的文字狱,其严酷程度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与此相关的文化高压政策,还包括禁止结社讲学、发布禁书令、大规模烧书和毁书等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清初那种因充满忧患意识和爱国激情所导致的思想界的锐意进取、探索和致用的学风被强行扭转了。同时,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随着时间推移而相继亡故,其后学即使继承了他们治学的某些方法,也因没有经历刀光血影的民族征服和亡国之痛而难以承袭前人的思想精髓。
清朝统治者在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同时,还采取怀柔手段,以促成与乾嘉盛世相适应的文化盛世。清廷重开科举考试,重新提倡理学,通过开设博学鸿辞科和组织编纂大型文化学术丛书招揽知识分子。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缮写《永乐大典》、武英殿刻书、设三通馆等措施,均属此种性质的举动。对学术文化片面性的大力倡导,加上康、雍以来较为长期的安定繁荣的环境,为乾嘉学者理头于朴学提供了可能性。
基于以上社会政治状况的客观压力和客观条件,以及知识分子主观的原因,他们转而专注于考据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乾嘉考据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来看,还可以从近因和远因两方面来理解乾嘉考据的形成原因。
学术思想发展的近因
指的是清初思想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宋明理学统治学术界已达六、七百年之久,明代中叶以后就不断遭到进步思想家的批评。明朝灭亡,宋明理学高谈性理所造成的空疏学风,更被认为是具有“空疏误国”的危害而被清初思想家所批判。与此相应,清初思想家提倡学以致用,崇尚实学,强调学术上的务实精神。他们认为,欲经世必先通经,欲通经必先考订经书的文字音义,把考证功夫结合在经世学术之中。其中最突出的是顾炎武。顾炎武治学讲治道、经术和博闻,主要方法就是考据。他认为命与仁,孔子也很少谈,性与天道,子贡亦未听说。孔子教人是要行己有耻,为学则应好古敏求。他说过:“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其论文,非有关于经旨世务者,皆谓之巧言。”顾炎武的考据方法主要是先详细占有材料,再由归纳例证中得出结论。他的名著《日知录》,就是主要以考据为研究方法的著作。从哲学意义上对理学的批判和在治学方式上的严谨务实,都是对理学的消极影响的一种否定。顾炎武被称为开启一代学风的宗师,他对乾嘉考据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必须指出的是,乾嘉学者继承顾炎武的主要是考据学的方法,而没有继承顾炎武学术的全部,特别是没有继承顾炎武以考据为手段为的是要讲求“治道”的目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理解顾炎武《日知录》的考据与乾嘉考据的上下关系,两者从起点到目的是有区别的。理学在清初已经被思想家们从根基上所撼动,理学的没落已不可避免。
尽管康熙和乾隆前期,程朱理学一直是科考的依据,清廷组织编纂了《性理精义》,并将《朱子全书》颁行太学,刊示诸生,这也不过是理学的回光返照。理学已难以吸引多数学者。同时,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某些进步的和超前的思想萌芽,在清代也失去了进一步成长发育的土壤。反映清初思想家观点的著述在乾嘉时代并不为人所理解和重视,其中一些优秀的著作甚至根本就没有刊行传世。
从以往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来看,每一个时代大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主潮,如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这种学术主潮的形成,一般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发展的脉络有密切关系。乾嘉考据的形成也同样如此。清初思想难以在新的政治条件下生存和壮大。顾炎武只好将希望寄托于“后起王者”。王夫之晚年不得不悄然遁于湘西石船山下,以著述了其余生。颜李学派的学说在康熙中后期的学术舞台上活跃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戛然而止,李塨在晚年背离了颜学而转向考据学。这表明清初思想在专制统治的严密文网中已经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土壤。康、乾时期理学的再倡也只是因为有了“御用”和“钦定”的包装。清初思想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黄宗羲另论)对理学进行了批判和总结,理学作为一个思想学术流派体系已经在理论思维领域中呈彻底瓦解之势。清朝统治者所建立复制的传统的专制统治的政治经济模式,也注定不可能诞生新的理论思潮。在文化高压之下,复归汉代经学,专注于训诂考证,以取代理学原来的统治地位,乃是大势所趋。顾炎武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费密主张:“学者必根源圣门,专守古经,以实志道。”乾嘉学者继承清初学者运用的考据方法,把目光转向遥远的“专门汉学”,既可脱离社会实际,又可回避学术上的理论原则问题,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学术思想发展的远因
应该从中国学术文化自身的发展渊源上来看。中国的学术文化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形成了庞大、繁杂的规模。几千年的创造和积累,包含了无数代学者经过辛勤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在客观上,需要来一次全面的整理。以经学和史学为代表,自先秦产生以来已有两千多年。各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是中国学术文化方面的宝贵财富,因为流传年代久远、缺乏有效的传抄和保存方式,以及历代战火动乱毁坏等原因,典籍本身存在文字内容上的错讹,史实记载上的歧异,以及部分及全部内容的散失等诸多问题,需要人们从事整理考证工作,然后宝贵的古代典籍才能被读懂和利用,历史记载的歧误伪托才能被指明,亡佚散失的篇章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被搜集和弥补。早在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等人对文献典籍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整理,为保存和后人利用古代典籍作出了重要贡献。两宋时期,考证工作已被众多著名学者所重视。司马光撰《通鉴考异》,详考在撰写《资治通鉴》时所用各书在史事记载上的差异,说明取舍理由。其他如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叶适《习学记言》、郑樵《通志·校仇略》,王应麟《因学纪闻》、黄震《黄氏日抄》等书,都有许多内容属考证性质。朱熹虽为大理学家,但他在考据学方面也有著述,并产生一定影响。明代心学泛滥,但仍不乏考据学方面的学者和著述,如梅鷟、胡应麟考辨伪书,焦竑、陈第研究音韵、文字等,考据之风的持续和考据方法的积累,是形成乾嘉时期考据臻于鼎盛状态的先决条件。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大规模系统整理,自刘向、歆之后还未曾有过。在继承前人考据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以期对传统文献作一番卓有成效的、带有总结性意义的整理,正是乾嘉学者所担当的历史重任。他们通过训诂注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丛书、类书、工具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和成绩。乾嘉考据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流派

顾炎武像
乾嘉考据学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其中特别是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答朱子德书》)。主张儒家义理在经书之中而不在经书之外;研究经典首重文字,而治文字必始于知声音。他所撰《日知录》、《音学五书》广征博考、言必有据,成为清代考据家的必读经典,也成为乾嘉学者经典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因此,顾炎武被公认为是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乾嘉考据学,一般说来可以分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影响
乾嘉考据学的产生虽然说与清代文化专制有关,但是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做出的贡献应该说是巨大的。
一是具有比较踏实的科学态度,发展了客观而精密的研究方法,即考据法;
二是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儒家经典进行了整理训释;
三是诞生了一大批训诂名著。
当然乾嘉考据学也有其缺点:他们的研究领域狭小,局限在儒家经典的范围内,不接触现实,不研究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也不敢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研究的方法陷于孤立、静止,注意微观研究,忽视宏观研究。因此,虽然对古代典籍爬梳考证,做出了成绩,却不能提供新鲜理论和有系统的思想体系,也不易接受、消化西方刚传来的科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