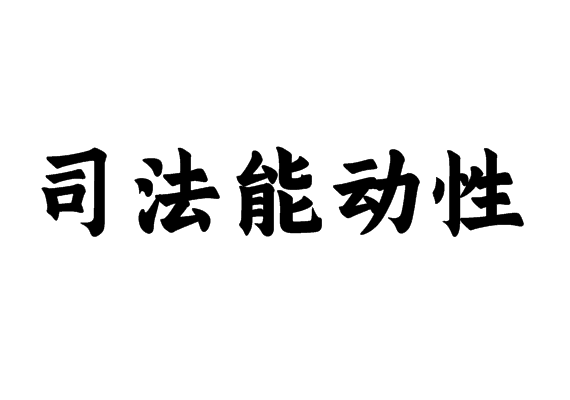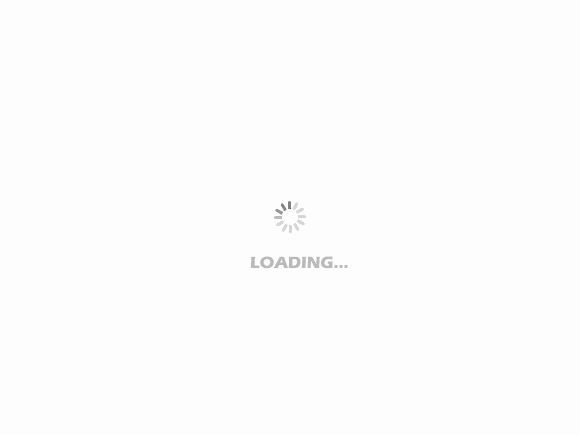司法能动性( Judicial Activism,又译司法能动主义、司法积极主义),指的是对美国司法制度中审判行为的一种见解。司法能动性的基本宗旨是,法官应该审判案件而不是回避案件,并且要广泛的运用他们的权力,尤其是通过扩大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去促进公平——即保护人的尊严。能动主义的法官有义务为各种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通过运用手中的权力,尤其是运用将抽象概括的宪法保障加以具体化的权力去这样做。
精选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荐
司法能动性相关的文章
蚜虫(英文名:Aphid),是球蚜总科(Adelgoidea)和蚜总科(Aphidoidea)昆虫的统称,又称腻虫、密虫,隶属于节肢动物门昆虫纲半翅目,包括球蚜科、根瘤蚜科、纩蚜科、平翅绵蚜科、扁蚜科、瘿绵蚜科、群蚜科、毛管蚜科、斑蚜科、毛蚜科、大蚜科、短痣蚜科和蚜科。蚜虫体长0.5~7.5mm,大
风热,是病证名,风和热相结合的病邪,临床表现为发热重、恶寒较轻、咳嗽、口渴、舌边尖红、苔微黄、脉浮数,甚则口燥、目赤、咽痛、衄血等。是风热之邪犯表、肺气失和所致。治以疏风清热为主。
汉明帝永平五年(62年),班超举家迁往雒阳(今河南洛阳),日常以替人抄书维持家庭生活。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以假司马的身份跟随奉车都尉窦固前往边塞,后跟随从事郭恂前往西域。他们辗转停留在西域三十多年,联络各国以孤立匈奴,对国家的巩固统一做出突出贡献。永宁七年(95年),班超被朝廷封为定远侯,后人
液氨,又称为无水氨,是一种无色液体,有强烈刺激性气味。氨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为运输及储存便利,通常将气态的氨气通过加压或冷却得到液态氨。液氨易溶于水,溶于水后形成铵根离子NH4+、氢氧根离子OH-,溶液呈碱性。液氨多储于耐压钢瓶或钢槽中,且不能与乙醛、丙烯醛、硼等物质共存。液氨在工业上应用广泛,具有腐蚀性且容易挥发,所以其化学事故发生率很高。

尚可名片
这家伙太懒了,什么都没写!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