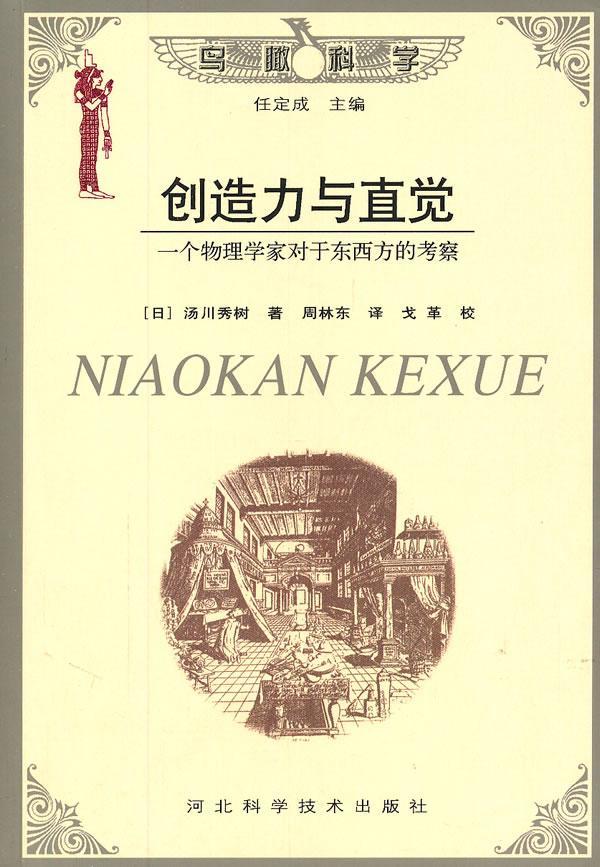表现形式

汤川秀树
在我自己的物理学领域中,当某人发现了某种新的自然现象或某种新的事实时,或是当某人发现了一条新的原理、一条新的自然定律时,创造力就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多亏这些发现,我们对于自然现象的理解或认识才能得到一个很大的发跃。被纳入自然定律中的那种我们对大自然的理解发展成一个包括了这些定律的理论体系,结果就可以把一个较大范围内的事实理解成一个整体。
在很多情况下,创造力是按它的结果来判断的。
例如,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原理。连那些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相对原理的人们也相信爱因斯坦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而且相信这儿发生的是一种创造轿车的了不起的表现。 当人们从爱因斯坦的传记中读到他年轻时并没有显示出特殊的才华时,或者当读到他某门功课考不及格时,人们对于他的惊叹更是有增无减。假如爱因斯坦当时在班上总是首屈一指的,人们的印象就不会那么深刻。想到后来做出伟大发现的人至少有过一次考试不及格。这常常会使人们对自己非常得意。但是,假如他没有做出伟大发现,假如他没有成为一个著名的科学家,那么最后的评语就会是,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没什么出息。
以成败论英雄也许是非常自然的,但是这却无助于阐明创造力的本质。人们倒是应当考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创造力的表现,创造力表现出来之前的事态如何,以及在此以前创造力一直隐藏在什么地方
创造力不是一种天外飞来的东西。遗传、环境等等无疑都会起到它们的作用,但是,不管人们多么想显示创造力,最重要的问题却是这种显示创造力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某种隐藏着的东西,潜伏着的东西,将会显露出来,表现出来。
因此,我觉得,创造力的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创造力隐藏在什么地方以及通过何种手段才能使它发挥出来的问题。
天才出现
17世纪时曾经涌现出许多天才。在一百年的时间内,出现了非常之多的天才--可以说是非凡的天才--从培根、伽利略、开普勒和笛卡尔,一直到牛顿和莱布尼兹。 
汤川秀树
再举一个情况相同的日常生活的例子。在学校里,常常会发现在某一两个年级中突然出现许多比较杰出的年轻人,接着而来的是一个空白时期,过不久又会有另一次同样的突然出现。
我猜想,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其中一个很容易把握的理由就是心理作用。一些勤奋好学而成绩优异的同班同学的出现,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一种要和他们竞争的促进或刺激。这种影响也许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同样,学者们似乎也在较长的时间内--在若干年乃至一个世纪中--互相发生巨大的影响并从而源源不断地产生出伟大的天才。
束缚的思维
当回顾我自己的一生时,我发现自己必须完成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任务已经一年一年地增多了。现在只要可能我就尽量不接受这一类的任务,但是这样的任务还是太多了。
最主要的是信息太多。潮涌而来的气死人的新刺激使人没有从容思考问题的余地了。当时人们--不得不--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上来。
我特别感到棘手的是,这种信息来到时已经是处理过的标准化了的。
当传来的信息量已经太多时,就根本不能再照原样提供它们了。单独一人整理这种信息,要花费巨大的劳力。实际上,无论好坏--在许多情况下是坏的--这种信息是已经给我们整理好了的。例如,报纸上的和电视上的新闻就是这种处理过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方便,我们就原封不动地接受这种东西。这种做法渐渐地变成了习惯;这似乎使生活更舒坦了些,不过这样一来,也不断增加了自己对别人的依赖性。
与此同时,不管由谁来负责整理信息,整理的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方法或某种框架的存在。即使当一个人亲自整理信息时,他只要在一个固定框架内思考问题,那就不会有创造力。一切重大的创造都从打破这种固定框架开始,或是从改变这种框架本身开始。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创造力,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全力以赴埋头干一件事,而不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任务和那些日常生活要求我们注意的信息洪水。换言之,需要的就是那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韧性。
表现出创造力的物理学家们,通常都是以非凡的--甚至是人们可能会认为几乎不必要的--韧性从事一个特殊课题的研究。
习惯、模仿和创造力
各种习惯在我们心里牢牢地扎下了根,形成一种固定的体系,而当意识接触到无法纳入这种习惯体系之中的什么东西时,意识常常就变得极其敏感起来。……
模仿就是创作某种已经存在的东西。我小时候,模仿比我大三岁的哥哥吃饭的样子。我哥哥就坐在我的对面。他用右手拿筷子,所以我就用左手拿筷子,认为这是在确切地模仿他。有一次,我母亲注 意到了这种情况,于是我才改用了右手,但是,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我至今用筷子还用得很不灵便。事实上,我往往因为把筷子攥在拳头中而逗人发笑。
我倒并不在乎受人嘲笑,但是,当我有什么外国客人并带他上日本式饭馆去的时候,那就尴尬了。由于客人经常要我给他表演正确使用筷子的方法,因此我不得不带我的妻子前去;她使用筷子非常熟练,于是我就告诉客人去跟她学。不久我就看过客人能够正确使用筷子了,而我自己却依然笨手笨脚。我感到难为情,但是即使我努力正确地使用筷子也坚持不了十分钟。
模仿似乎毫无用处,然而人们却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它。这样的人决非不可能成为专家。但是,有时创造力偏偏就起源于这种重复过程之中。
从广义上来说,这种模仿会变成为记忆。人是有记忆力的,他通过记忆力来把自己的经验储存起来。没有这种记忆的储存,创造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同我们已知道的,记忆意味着储存经验,而且在需要的时候再创造它们--重复它们。回忆本身就是一种重复,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似乎没有任何创造的成分。至于回忆为什么有时会带来创造,这却还没有真正搞清楚。
家教故事

汤川秀树
外祖父驹橘在明治之前是每日守备和歌山城的武士,汉学涵养丰富;明治以后学习西学,一直到晚年都在购读英文的《伦敦时报》。 汤川家的孩子从五六岁起就随祖父读汉书。每晚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这对儿童确是件苦差,但当他精通汉字后,读起大人的书就毫不费力了。 汤川秀树的父亲琢治,是地质地理方面的专家,多次访问欧洲,兴趣广泛,也喜好书画,几次到中国研究古书、古董与石佛。琢治的特点是,一旦对什么热衷着迷,就要收集其所有的文献,否则决不罢休。迷上围棋,就买尽围棋方面的书。汤川家中随处可见各学科的书籍。“家里泛滥的书抓住了我,给了我想像的翅膀。”汤川秀树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泛读了许多文学书使汤川秀树成了一位文学少年。琢治从未强迫孩子学习,并认为为名次学习最为愚劣。他尊重孩子们的独立人格,希望孩子们可以深入研究适合自己素质与爱好的学问。
汤川秀树母亲的教育原则是对孩子们公平,并希望让每个孩子都成为学者。父亲一度对内向性格的汤川秀树是否上大学表示怀疑,很少反驳丈夫的母亲开口说:“这样做不公平。我要公平对待每个孩子。”
母亲的话不多,不爱对幼年的孩子说教,但无论她手里做着什么,只要孩子一问:“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她一定会停下手里的活,耐心地回答孩子。汤川秀树评价说,他的母亲是女性中少有的思考力丰富的人。母亲就学于东洋英和女校,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学过英文的女性。在东京时,她每周一次出外参加烹调学习班,并喜爱文学。到京都后,随着孩子的增多,她也和京都的主妇们一样,不多抛头露面;但她仍长期购读《妇女之友》等代表先进思想的杂志。专心家务的母亲生前在遗言中写道:愿意提供自己的大脑做科学解剖。 汤川秀树在中学读书时,校长的独特入学祝辞是:“今天开始我将视诸君为绅士。”
在父亲琢治犹豫着是否送汤川秀树入学时,森外三郎校长作了这样令琢治下决心的保证:“汤川秀树的头脑是属于在飞跃中转动的类型,他的构思敏锐,数学上有天才之处,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中学时幽默的数学老师竹中马吉使汤川秀树着迷于数学;高中时物理老师森总之助,更使汤川秀树成为“书虫”。他几乎隔几天就要去一次专卖欧美版书籍的刃善京都书店,他买得最多的是数学书和物理书。
“我是在思考的飞跃中发现喜悦的人。”汤川秀树在摘取诺贝尔桂冠时,确认了老师过去的评价。
一段自述
我在上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明确地下定决心要成为物理学家。其原因之一,是我认为自己欠缺成为动物或植物研究工作者的素质。从幼年时代到少年时代,我也像一般人一样对昆虫有兴趣。那时,我住在京都市内,和今天不一样,身边就有昆虫。有树丛的庭院就是各种各样昆虫的栖息之所。我还在附近的皇宫树林里捉过独角仙,拿回家来放在点心盒里饲养。但是,同动物打交道没有更大的进展。对植物的关心就更淡薄了。草木的名字听了过后,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很久以后,我写起和歌来。但是不知道植物和鸟儿的名字,常常感到伤脑筋。 因此,我没有成为生物学家。但是,有一个关于生物的疑问,从少年时代起直到今天,始终留在我的心中不曾消失,尽管在这过程中,它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从我上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它就开始产生了。上生物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作了关于进化论的初步讲解。首先介绍了拉马克(J.B.Lamarck)的器官用进废退说。他认为,生物如果经常使用各种器官,它们就逐渐发达,生物则因此而进化下去。这种观点,对于中学生的我,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老师却认为这种说法要不得。他认为,生物出生以后,后天获得的能力是不遗传的,对于进化不起作用。于是,他接着开始讲解达尔文的进化论,说:同类的生物之间进行着生存竞争,在这过程中,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者,其子孙也将繁衍增殖;生物是靠这种自然淘汰而进化的。这对我说来,难于理解得多。回家以后,我仍然拼命地思考,但还是不能理解。 很久以后,我更多地懂得了物理学之后,试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注意到:大概是因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包含着统计上的考察,所以才难于理解的吧。拉马克那样的思维方法是根据以下情况得出物种进化结论的,即:生物的一个个的个体在生存期间是遵循着因果法则在变化的。该个体又遵循着某种因果法则将那变化遗传给它下一代的一个个的个体。这正是古典物理学家的思维方法。当然在这里,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存在着个别因果律。在这一点上,达尔文那样的思维方法--作为多数个体集团的物种总体的变化倾向就成问题了。在物理学方面,作为与此相对应的思维方法,是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大约20年后才建立了被称作古典统计力学这一学科。在这里,中心问题是:以建立了个别因果律的古典力学为基础,而从统计上去解释热力学的各种现象。但是,拉马克那样的进化论,和物理学的情况不同,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古典力学的任务,这是很显然的。取而代之的究竟是什么呢?那时,我这个中学生并不很了解物理学和生理学,当然不可能那样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的朴素的疑问,不久不是就面临了应该发展成为上述那种形式的命运了吗!后来,我仍然在思考那个问题。 20世纪初,在生物领域出现了突然变异说。令人惊奇的是,它同物理领域量子论的提出几乎是同时。尽管后者意味着发现了微观过程的不连续性,但是对于这样的过程,当时我仍然认为存在着个别因果律的吧。直到20多年后建立起了量子力学,对于一个个的微观过程,我才终于不得不放弃因果律的想法。这是因为我明白了;由于同样原因开始的微观过程,结果却各不相同,因此只有承认根据非常多的过程所获得的结果而归纳出的关于分布情况的规律。这意味着用统计因果律置换了个别因果律。这是一种非决定论。在我了解了量子力学及其统计解释后不久,就是说在1930年,我甚至在想象:在生物领域难道也有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吗?不过,所谓突然变异是罕见的现象。在一般条件下,非如此的情况则是压倒多数。正因为如此,生物的种才得以存续下来。和量子力学的情况不同,遗传现象具有强烈的决定论性质。不仅如此,即使偶尔见到偶然发生的突然变异,它同量子力学的非决定性似乎也不是同种的东西。到了1940年,我读了薛定谔(E.Schrodinger)的名著《生命是什么?》以后,才明白了这个问题。他是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他反对以马克斯·玻恩(Max Born)、海森堡(W.K.Heisenberg)和尼尔斯·玻尔(N.Bohr)为代表的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即承认微观物理现象的非决定性的统计解释,而主张立足于波动一元论的决定论。在这场论争中,正统派一方处于优势,绝大多数年轻的物理学家都奔向了该阵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上面谈到的那样,一时我当然也认为在生物领域也像量子力学似地,非决定性是重要的。在正统派中,特别是玻尔,把为理解微观物理现象而引进的互补性概念类推地带入了对生命现象的解释之中。但是这里所说的互补性意味着在无生物的物理现象中看不到的新的性质。因此,受其影响而从物理学转而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德尔布吕克(Max Deforuck)期待着能够发现与物理法则不同的法则。但是其后的事态进展却与他的预想相反。就是说,薛定谔在德尔布吕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已经拓展了如上所述的决定论见解。扩而大之,1953年沃森(J.D.Watson)和克里克(F.H.C.Crick)建立了DNA模型以后的情况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在这里可以看出180度的大改变。因为我明白了:在量子力学的解释上曾处于劣势的薛定谔一方,在解释生命现象上却较玻尔显然有先见之明。不仅如此,还明白了:按照分子水平上的朴素实在论、机械论的思维方法就能够充分理解遗传现象。这是笛卡儿式的“动物机械论”的现代版。当然,在它的背后确实有着电子水平的量子力学机械论。不过,我知道,不深入到这种程度也无妨。这从物理学方面来看,甚至令人有翻了个儿之感。但是,在生命现象研究方面,还有广阔的未知领域展现在前方。尤其是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动物的神经系统,今后将会多次地迎来新局面的吧。而且,在某方面不是将会面临不辜负玻尔和德尔布吕克当初的期待的新情况的吗!似乎也有专家作如是想。这是后话。 说到这里,回顾一下便可以发现,我从中学时代以来关于进化论的朴素的疑问,至今仍未打消。反而又增添了其后的新的疑问。我记得大约是在大学时代,我读过海克尔(E.H.Haeckel)的著名的《宇宙之谜》。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899年。所以,关于物质和宇宙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古典物理学基础上,从今天看来,是完全过时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一点或者他的一元论哲学却总是好的。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主张的说服力,尽管我未能十分理解。这种主张贯穿在关于动物发生的详细得甚至有些烦琐的叙述之中。用一句话来说,它就是:个体的发生是重复系统的发生。长年以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从达尔文那样的进化论中,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其后,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奇怪的是,哪一本书也没有触及这个问题。而且,尽管我试向各方面的专家谈起过我的朴素的疑问或者我这样的外行想法,却都没有反应。近来,我仍一而再地重复这种经验。不过,稿纸已经写完,留待另外的机会再谈这个问题吧。在这里,我只是想坦率地承认:一个物理学家很久很久以来,关于生物的进化一直抱有朴素的疑问这一事实。生物学尽管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直到今天,对于我长年的疑问仍未给出能够令人满意的、一语中的的回答,却令人焦躁。